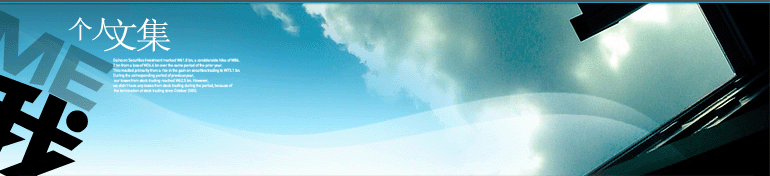|
在北方,冬天很冷。
惡劣的天氣造就了北方人忍耐的個性,很多事情,被忍受著。霜生在距離北極村很近的一個小鎮上,那裡有一個煤礦,所有的人都住在成排的一樣的磚房裡。白天男人們下井采煤,晚上一身髒兮兮的回家坐在熱炕上吃女人做的酸菜白肉。女人們在飯後抱著孩子去鎮中央的禮堂看電影,電影票一毛錢一張。
媽媽生霜的時候爸爸出車不在家,鄰居把媽媽送到小鎮上唯一的一家小醫院,然後霜降生了。當醫生告訴媽媽生下一個女孩子的時候,媽媽失望的閉上了眼睛。醫生把小霜抱給媽媽,小霜粉紅的臉上冰涼冰涼的,那時候是農歷二月,天氣還是冷得要命。媽媽看著熟睡著的孩子,心裡說,孩子呀,為什麼你是個女孩子呢?醫生認識這個小鎮上的所有人,她知道這孩子生錯了性別,這決定了她的悲慘命運。霜生在一個冬夜,第二天媽媽從病床上醒來的時候,看見窗戶上結了一層漂亮的霜花,她給女兒取名霜。
由於媽媽生了一個女兒,重男輕女的奶奶沒有來伺候月子,守寡多年的姥姥大老遠的從幾十公裡外的另一個鎮子趕來照顧產後虛弱的媽媽。霜很少哭,晚上吃飽了,整個夜裡都不會醒來。白天霜靜靜地躺在小被子裡,眼睛滴溜溜得亂轉。姥姥哭著說,這孩子懂事,不哭也不鬧,可是她的命怎麼這麼苦哇,她奶奶怎麼不疼這麼聽話的孩子呢。媽媽躺在床上流著眼淚,眼淚順著臉頰流下來滲進枕頭裡。
霜生下來的第十三天,礦上送來了消息。開車去外地送煤的爸爸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連人帶車滑下了山坡,發現的時候,屍體已經被大雪掩埋了。媽媽和姥姥抱頭痛哭,聞訊趕來的奶奶哭著用一根木棍追打媽媽,嘴裡一只喊著,掃把星,掃把星,還我兒子。小霜被小被子緊緊地包裹著躺在熱乎乎的炕上,眼睛望著糊滿了報紙的頂棚。奶奶轉身用木棍打躺在炕上的小霜,你這個小掃把星,都是你,索命呀,你生下來就把你爸方死了,你們兩個大小掃把星,還我兒子來呀。姥姥死死的抱著安靜的小霜,淚流滿面,棍子毫不留情的落在姥姥瘦弱的背上。奶奶悲憤交加,一氣之下跟兒媳婦斷絕了關系。霜是女孩子,奶奶讓兒媳婦帶回娘家去,一輩子都不要見到她們母女倆。
媽媽還在月子裡,倔強的姥姥就僱了一輛雪橇把她們母子接回了家。人家說,在月子裡的女人最怕傷身子,媽媽在月子裡受了涼,從此落下了有一點累著了就會腰疼的毛病。
霜十一個月的時候,媽媽決定去哈爾濱進修,她決定給女兒一個美好的人生。姥姥抱著小霜,小心翼翼的走在結了冰的路上,媽媽用一塊長長的彩條圖案的頭巾將自己的臉包裹起來,拎著包沈默地走在前面。到了車站,媽媽脫掉厚厚的棉手套,輕輕的撫摸著小霜的小臉,小霜對著媽媽笑個不停。
小霜在姥姥身邊快樂的長大,雖然身邊沒有什麼小伙伴,但是姥姥家有大狗大黃和一群生好多蛋的雞。夏天,霜跟著姥姥在菜園子裡拔草,摘熟了的西紅柿吃,把黃瓜摘下來放在水缸裡,在爐子上烤鮮嫩的玉米和小個的土豆,還去跟著姥姥進雞捨撿熱乎乎的剛生下來的蛋。春節的時候,姥姥給霜買新衣服,在大年初一的早上穿上了跟著姥姥去親戚家拜年。有時候霜問姥姥,爸爸呢,為什麼爸爸從來不來看我。姥姥告訴霜,爸爸就住在天上,那裡溫暖,不像這裡這麼冷,有一天你也會去那裡,那時候你們就能見面了。霜不是一個調皮的孩子,她不像一般的孩子經常哭鬧。高興的時候她會微笑,不高興的時候就低著頭不搭理任何人。霜喜歡折紙,用紙折房子、衣服、小青蛙、小貓、飛機,這些就是霜的玩具。
一晃三年過去了,霜已經會寫很多字,會被很多首詩了,媽媽進修結業回來了。姥姥把霜叫進屋子裡來讓她跟面前的女人叫媽媽,那個女人微笑著蹲下身子張開了手臂,霜卻認生的躲進了姥姥的背後。媽媽的微笑僵硬在了臉上,眼淚悄無聲息的流了下來。
四歲的霜不情願的跟著媽媽來到了哈爾濱,媽媽帶著霜到處玩。媽媽給霜買會叮咚響的不倒翁,五分錢一根的冰棍很甜,霜吃的滿手粘乎乎的。媽媽在一家化工廠的實驗室裡工作,她把霜送進了廠托兒所。
在那裡有很多的小朋友和很多的玩具,可是霜最喜歡大門口的那座圓形花壇,裡面開滿鮮花。看門的老爺爺很喜歡霜,這孩子雖然不怎麼愛說話,可是卻很乖巧。看門老爺爺在他住的房子後面種了一小塊地,種了一些黃瓜和西紅柿。很多小朋友總是偷偷得到他的小菜園裡摘小黃瓜和青的西紅柿,只有霜每次都幫他除草、澆水。霜常常一個人蹲在黃瓜架下悄悄的說話,沒有人知道她說了些什麼,有人靠近的時候她就不說了。
一年之後,媽媽在一次試驗中引爆了化學藥品,只是小小的爆炸,可是卻接連引爆了實驗室裡其他的易燃藥品,整個實驗室著起了大火。大家把火撲滅之後,只看到一具燒焦的屍體。姥姥千裡迢迢從小鎮趕來哈爾濱,在火葬場裡,所有的人都在痛哭,霜坐在傷心的姥姥懷裡,抱著姥姥的脖子一聲不吭。姥姥突然發作,把霜放在地上打她的屁股,你為什麼不哭,現在你的媽媽也死了,你就不會哭一聲嗎?你爸死的時候你小,現在你媽也死了,你為什麼不哭呀。媽媽的同事抱過小霜,把姥姥攙到椅子上坐下說,別嚇著了孩子,她還什麼都不懂呢,別嚇著她呀。霜掙脫了阿姨的懷抱撲進姥姥的懷抱,姥姥抱緊霜小小的身體,你怎麼這麼命苦呀,不是你方得他們見了閻王,是你天生命苦呀,不是你的錯呀。
霜上高二那年,姥姥去世了,這世界最後一個愛霜的人也走了。霜通知了遠在南京的唯一的舅舅,等舅舅趕回來的時候霜已經將姥姥火葬了。霜把骨灰交給了舅舅,就轉身離開了。
媽媽死的時候給霜留下了一筆錢,姥姥也留給了霜一些,足夠霜一直到大學畢業。霜順利的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藝術院校,學習展示設計。在學校裡,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城市裡的人不如小鎮上的居民來的熱情和純朴。大家互不乾涉,每個人似乎都穿了一層互甲,防備著身邊的每一個人。霜還是一個人,一個人去上課,一個人去圖書館,一個人坐長途車去寫生,一個人在假期裡呆在空蕩蕩的宿捨裡。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霜在一家設計公司找到一份設計助理的兼職工作,嘗試做一些簡單的設計。由於工作的關系,霜在外面租了一間不錯的房子,花掉了她所有的工資,可是值得。霜在地面上鋪了一層地毯,然後買了一張雙人床墊,一張三十公分高的小桌子,一盞黑色的臺燈和幾個抱枕,用黑色的套子套起來。
霜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之後就昇任了設計師,雖然還不是很有名氣,但是老板很賞識她的纔華。霜的作品裡總是透著冷靜和殘酷,而這種品位在這個社會漸漸變成大家願意接受的風格。
每當過節放假的時候,霜就一個人去旅行。假期長她就去很遠的地方,她去過西藏、海南、雲南、廣西、陝北,但是她從來不去北方。她終於知道爸爸、媽媽和姥姥相繼去了哪裡,她知道在這個空間裡她再也不可能和他們相見。可是霜相信他們會再見面,當她也死了之後。
霜接了一個設計,給一家英國時裝品牌在北京的專賣店做店面設計。和她接洽的是那家公司北京區的藝術總監,堅,一個29歲的男人。堅告訴霜,服裝的風格是時尚、獨立,主要銷售群是高級白領。一個星期後,霜帶著設計稿來找堅。霜設計的店面是很寬大的廳堂,大幅的落地門窗。牆壁是深色的,掛著一些同樣色調深重的時裝廣告畫,是經過處理的。所有的家具都是銀色的金屬所制,透著冰冷和堅硬。頂燈的光打得很強,照在排列在牆邊的衣架上。堅最後通過了霜的設計,基本上沒有做任何的改動。定稿之後,堅問霜,為什麼要設計得這麼冷硬。霜回答他,高級白領女性,如果沒有一點冷酷的感覺就難以服眾,而那些坐在高級主管位置上的女性,也正在極力掩蓋自己身為女性的軟弱和脆弱。衣服成了掩蓋本性的畫皮,在這個社會卻成為合理的個性。
第一家專賣店裝修完畢的那個晚上,堅請霜吃晚飯。堅去霜的公司接她的時候兩個人還不餓,索性找了一家酒吧喝酒。
霜沈默的坐在堅的對面喝光了手上的伏特加,加了冰的淡黃色液體在滑下喉嚨的瞬間給神經帶來瞬間的冰凍感覺,之後在胃裡面一點點地燃燒。堅看著一言不發的霜,不知道該說什麼,於是問霜,你的家人好嗎?霜抬起頭看堅,我的家人都死了,分別在我剛出上的第十三天、五歲和十七歲的時候。
堅發現自己問了一個多麼愚蠢的問題,感覺很愧疚。
霜再次喝光了杯中的酒對堅說,不要覺得抱歉,這對我來說不一個禁忌的話題。他們離開我去了另一個地方,他們在那裡等著我,有一天我會和他們見面,我們會像所有家庭一樣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霜微笑著喝掉手上杯子裡的酒。她不斷地給自己的杯子裡倒酒,很快的喝光,然後再倒,仿佛那不是酒,是痛苦和罪孽。
酒精在霜的胃裡無情的燃燒著,連帶燒灼著她沈默的神經,使它復蘇。霜握著杯子繼續說,今天她打算做一個徹頭徹尾的傾訴者。他們走的時候我沒有哭,爸爸死的時候我剛出生,我還不知道什麼是難過。媽媽死的時候我五歲,那時候我已經知道了他們去了什麼地方,我覺得我只有等待,別無選擇。姥姥去世的時候我更加堅信,他們在某一個地方集合,等待著我。有時候我問自己為什麼當有人離開我的時候我從來不難過,最後我告訴自己,任何人的生和死,來和去都不是我能選擇的。
撕去因為生存而裹在身上的偽裝,每一個人都是赤裸裸的。有快樂和幸福的,不論是傷口還是笑容,都暴露在明晃晃的視線下,卻從不感到狼狽。
堅從小在爸爸媽媽身邊長大,他不能體會那種失去親人的照顧和笑語是一種怎樣的失落和疼痛。堅看著霜一個人喝光了整瓶的伏特加,斷斷續續的講述著自己的經歷,最後醉倒在座位上安靜的睡著了。
霜的臉上一片紅雲,睡得就像一個洋娃娃。堅的心裡被某種莫名的東西填滿,阻塞在喉嚨裡好像要爆炸。他從心裡心疼眼前這個外表冷漠不所謂,內心卻異常敏感脆弱的女孩。
一個人被痛苦壓抑了太久,就會像一個飽脹的氣球,一直吹氣就會爆炸,需要不斷的釋放。眼前這個年輕的女孩太久沒有釋放過,她已經快崩潰了。她孤獨的生活在諾大的城市,在別人歡聚的時候,她獨自一人履行在路上,逃避那些歡樂的場面。在旅途中,她遇到的都是和她一樣的旅行的人,她不會被溫暖刺傷。
她所遭遇的都是虛幻的過往,隨時的出現和消失。她是一個需要照顧的女孩,有那麼一刻堅想搖醒她並且告訴她,他願意照顧她。可是堅知道他並不能保證會照顧她一輩子,這個女孩心裡的傷只能用永恆去治療,而他不能保證一定做得到。任何一種有可能會背叛的誓言對她來說,只能是一次更深的傷害。而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病態世界,永恆僅僅是理想中的不可兌現的童話。
然而這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我們不能選擇的,比如父母兄弟,比如上司同事,比如經歷災難,甚至,愛情和婚姻。還有,信守諾言。堅清醒的知道,霜說的『別無選擇』的無奈和妥協。
霜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陌生的房間裡,窗外是一片寂靜的黑暗。堅不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最後把她帶來自己的公寓。霜光著腳走出房間,堅穿著軟薄的純棉深米色長褲和白色襯衣坐在亞麻布藝沙發上,手上握著一杯加了冰的威士忌。你醒了,真快。我在哪?我的公寓,你喝多了。
霜走過來坐在堅對面的地板上,手扶著快裂開的腦袋。要不要吃點東西,你晚上什麼都沒有吃,堅放下手上的酒杯問。好。
堅走進廚房,十分鍾後端出了兩碗面,滑溜筋道的面條上面蓋著一個荷包蛋和幾片三明治火腿。湊合吃吧,我這裡只有這個。霜什麼都不說拿起筷子不客氣地開始吃起來,堅微笑著看著霜,然後低下頭慢慢的吃自己的面。霜很快吃完了自己的面,還有沒有?還想吃?霜用力的點頭。堅把自己的碗推到霜的面前,不嫌棄的話,吃我的吧,我不是很餓。霜深深地看了堅一眼端過碗吃了起來。
霜很快吃光了堅那碗面條,然後站起來主動拿起碗去廚房刷洗。堅打開電視,深夜正在播放不知道哪個國家的電影,一個女人站在廚房用力的刷洗鍋臺,嘴裡大聲的抱怨著,懶惰的丈夫正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沒聽到似的看報紙。堅聽著廚房傳來的嘩嘩的水聲,不自覺的微笑起來。離開父母一個人生活這麼久,通常家裡只有水箱漏水的滴答聲。
後來霜經常跑到堅的公寓來,堅回來得晚了,就看見霜坐在門口抱著膝蓋睡著了,最後索性配了一把鑰匙給霜。有時候堅下班回來,霜在廚房做飯,堅洗了澡換了衣服出來霜已經把飯菜擺放在餐桌上,兩個人一邊看電視一邊吃飯,誰也不說話。有時候霜會留下來過夜,固執的睡在沙發上,早上堅醒來的時候霜已經離開了,餐桌上放著冒著熱氣的早餐。
一天晚飯後,霜縮在沙發上一邊看電視一邊啃一個苹果,膝蓋上還攤著一本時裝雜志。堅坐在沙發的另一邊,看著霜,若有所思。堅關掉電視對霜說,我們結婚吧。霜咬著苹果轉過頭來驚詫地看他,這決定顯然太突然了。我知道我的這個決定對你來說很突然,但是我相信我們會相處得很好。霜放下手上的苹果問堅,你愛我嗎?是的,我愛你,我一點一點直到現在深深地愛上你了。霜突然跳下沙發抓起放在門口的包跑了出去,堅根本來不及阻止。堅追到樓下馬路上,看著霜跳上一輛出租車走掉了。
堅打電話到霜的公司去找她,公司的人說霜請了病假。堅打聽了她的住址去找她,房門緊閉,鄰居說已經好幾天沒有人回來了。
堅找不到霜,他決定取她,卻一點都不了解她的生活,可是他是真的很想取她跟她生活在一起。
她心裡有一塊傷疤,那是時間刻上去的痕跡。一切事物對她來說都太虛幻,太不安全,他們隨時會離開她,而她堅強的外面下滿是恐懼,她卻告訴自己別無選擇。是吧,也許真的別無選擇,生老病死,生離死別,這些都是我們所不能選擇的,而她卻排斥了一切可能的幸福。在他想要取她給她依靠的時候,她卻逃了,也許她去尋找答案。面對選擇,她別無選擇的選擇了逃避和封閉自己。
堅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唯一的聲音就是衛生間水箱漏水的滴答聲。房間裡沒有任何一件東西是屬於霜的,哪怕是一支筆,一面小鏡子,堅卻分明聞到了除自己以外的屬於另一個人味道,霜的味道。
似乎除了等待,沒有任何的辦法。堅靜靜的等待,等待霜回來。他相信,她最後會別無選擇的回來。在等待中,堅繼續他的工作和生活,還有想念霜。
作於2002年9月14日--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