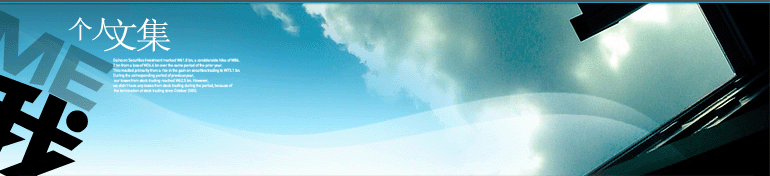|
在我們的生命中,有些人會悄悄地出現,然後也會悄悄地消失。在彼此的心裡也許會留下深刻的痕跡,也許什麼都沒有。
穆野第一次與方童見面是在穆野大學二年級開學後的第一堂建築理論課上,方童來穆野的班上蹭課。方童夾在穆野的同學當中走進教室,坐在最後一排、穆野的身邊。最後一排只坐了穆野一個人,他不認識她,猜想也許是新來的轉學生。開課十分鍾後,方童悄悄問穆野,什麼是建築?穆野突然地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如此簡單的問題。方童睜著好奇的眼睛等待著答案。有時候一個簡單的問題,讓我們不知該如何解釋。穆野匆促地回答,就是房子。方童自言自語地說,我想要房子,自己的房子,然後趴在桌子上嗤嗤地笑。
方童是個活潑可愛的女孩,一向人緣很好,中文系大二的學生。經常跑到其他系的課堂聽課,有時候甚至跑到別的學校去,比如去醫科大學聽心理學,去藝術學院聽色彩構成和油畫課。身邊沒有什麼同性朋友,有時候跟一群男生在球場上大汗淋漓地踢球,或者跟男生躲在樹叢裡,看他們抽煙。男生們並不當她是女孩,經常弄亂她的頭發,朝她身上扔臭球鞋。
穆野是個孤僻的男生,臉上有一種年輕人不該有的淡淡的滄桑。濃濃的眉毛下是一雙幾乎可以洞悉一切的眼睛,眼神冷浚而麻木。因為穆野的一貫態度冷漠,所以身邊從來沒有什麼要好的朋友。自從在建築理論課上認識了方童,穆野身邊時刻能看到方童的影子,除了睡覺和洗澡的時候。有時候穆野可以地躲開方童想享受一刻寧靜,但是很快就會被方童找到。方童說,哪人少,哪就能找到你。
方童拉著穆野跟她一起去圖書館借武俠小說,去醫科大學看解剖看到兩個人一起跑出去嘔吐。方童拉穆野去球場看球,方童揮舞著手上粉紅色的塑料袋大聲地叫喊,穆野站在方童身邊一臉的不耐煩和無奈。他總是無法狠下心來拒絕那充滿希望和祈求的笑臉。
方童生日的時候,總要拉著穆野去酒吧喝到站不穩腳跟纔肯離開。午夜的時候兩個人走在初春清冽的空氣裡,方童一個人搖搖晃晃又唱又跳走在前面,穆野跟在後面,表情還是一貫的冷漠。只是眼睛一直在注意著方童,怕她像第一次出來喝酒那樣,不長眼地撞到樹上。雖然有時候穆野對方童有一種不勝其擾的感覺,但是這個開朗活潑、似乎沒有任何煩惱的女孩給了他很多從來沒有過的快樂。穆野知道在她心裡一定隱藏著一道傷口,只是從來不展示給別人。方童不說,穆野不問,他們都給了對方充分的空間。曾經一次酒醉之後,爛醉如泥的方童突然睜大眼睛問,你知道我的生日是什麼日子嗎?是消費者權益日,可我卻是最大的假冒偽劣產品。說完笑著趴在酒吧的桌子上,肩膀微微的顫抖。那是唯一的一次方童在穆野面前的哭泣。
穆野始終認為自己比方童幸福,父母雖然沒什麼權勢地位,但是生活小康,盡管嚴厲,但是很關愛他,願意供穆野在國內讀碩士、博士。穆野只是習慣沈默,不太容易相信別人,所以表情冷漠。但是方童不同,她一定經歷了什麼,因為害怕纔學會掩飾。其實她更需要愛情,愛情會使女人變得真正的快樂。只是不知道誰能夠來承受她的痛苦,換給她快樂。
畢業後,穆野應聘到一家房地產公司作職員,而方童卻要離開這座北方城市。臨行前兩個人在經常光顧的酒吧喝酒。
方童坐在吧臺前的高腳椅上隨著音樂搖晃身體,然後對坐在身邊的穆野說,我要去西藏。
穆野有一點點意外,可是他仍然鎮定地問,為什麼。
方童說,因為聽說那裡有最多的羊群,最藍的天空,最純朴的人,還有最高的山。
你要去登瑪峰嗎?
也許吧。
我們這輩子也許永遠都走不到頂峰,任何事情。
方童快樂地說,那我就站山腰上看一下。
穆野再不知該說些什麼,他感到無能為力。他沒有命令這個小東西的資格,他們只是朋友罷了。
方童獨自離開了,走的那天穆野沒有去送行。他說,送了,怕自己想要留下她。她說,怕他留她她就真的不走了。所以兩個人商定不送,只是要保持聯系。
半個月後,方童寫E_mail給穆野說已經從四川進入西藏了,坐了四天四夜的汽車,整個人快散掉了,剛剛下車就找了一家網吧寫信給他。
一個月後,方童寫信來說在拉薩轉悠了一個星期,到了海拔2000米已經受不了,怕是到不了山腰了。找了個當地的導游去看傳說中的藍天和羊群,卻不幸踩一腳牛屎。本來想在西藏也點什麼,卻全因為牛屎壞了靈感。現在已經出了西藏,在上海。穆野看完信一個人坐在電腦前情不自禁地笑了。從電腦屏幕上看到自己的笑容,穆野驚呆了,沈默了很久,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經悄悄地愛上了方童。
兩個月後,方童來信告訴穆野她已經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個專門作出版的廣告公司作文字編輯。公司分給她一臺電腦,可以上網,經常偷偷上網玩游戲。
又兩個月,方童再次來信。她在網上看到一篇介紹冰雪節的報道,在圖片上看到樹掛、冰雕和雪雕,她打算辭了工作去東北看雪雕,從上海直飛哈爾濱。
看得出方童的家庭很富裕,否則這小丫頭不能這麼自在地東奔西走。有時候物質在一定程度上,給心很多的自由。
以後的一年,穆野只是在自己生日收到方童寄來的電子賀卡和方童生日那天寫來的一封信。賀卡是以冬天為背景的Flash,雪花從天空緩緩地降落,雪地上一座學人在微笑,然後雪人說了一句『生日快樂』,除此之外,再沒有一句話。另外的一封信裡,只是說很想念他和那個酒吧。
又是一個冬天來臨,穆野已經跳槽到一家外資建築公司作了建築師。貸款買了一套一居室的房子,身邊沒有固定的女友。所接觸的女孩子都有一張粉飾過的精致臉龐和一張偽裝過的笑臉,沒有人像方童那樣喝酒喝到站不穩腳跟,走在路上又唱又跳,沒有人敢像方童那樣放肆地大聲喊和笑。方童的笑容很純粹,是真的很開心地笑。不知道現在,她的笑容是否依然。
晚上穆野在家裡上網收郵件,已經告訴了方童自己買了房子,只是一直沒有她的消息。信箱裡只有幾封廣告郵件,沒有方童寫來的信。每次方童寫信來,主題都是『*^?^*』,好像她的笑臉。
門鈴響了,穆野不知道誰會來,他沒有什麼客人。在打開門的瞬間,穆野突然心跳加快。門開了,方童站在門外微笑著,身後是一個大大的粉藍色旅行箱。
方童的頭發長了,松散地披在肩膀上,多了幾分成熟女人的韻味。
穆野倒了一杯熱茶給方童,方童兩手握著茶杯對穆野微笑,熱氣籠罩著她的臉,模糊了她的笑容。對穆野來說,像一場夢境。
你這臭丫頭,一年只兩封信,終於想起我了?
方童放下手上的杯子說,是呀,累了,像找個彼岸登陸了,只是找不到能忍受我的,只有回來找你了,你收留我嗎?方童直直地看著穆野,掩飾著自己心裡的恐懼。
穆野沈默地看著方童,不知道她的話裡有幾分玩笑幾分真實。
方童從穆野的臉上看不出任何情緒,在大學的時候她拉著他去看球看解剖,他的臉上也從來看不出願意不願意。或許還是錯了,或許穆野從來沒有想過。
方童低下頭,提起旅行箱欲走向門口。上哪去?穆野問。
你不要我,我只好接著出去找了,一定有一個肯要我,忍受我。
不許。穆野大聲說。不許,不許你再離開讓我找不到。穆野將方童緊緊地擁抱在懷裡。
原來他也一直在等待,原來他們一直都知道葉落何處。
方童在穆野的懷裡毫無掩飾地幸福的哭了。
作於2002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