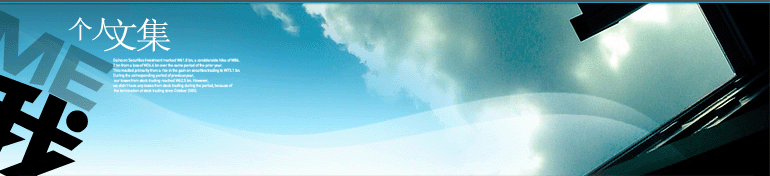|
夢夢的自白(1)
我姓孟,單名夢。據說出生之前我母親做了一個非常嚇人的夢,於是我便叫這麼奇怪的名字了——孟夢。他們習慣叫我夢夢。
因為那個夢的驚嚇,我母親不喜歡我,當小我兩歲的弟弟出生之後,父親也忽略我了,畢竟那是他孟家的『唯一』血脈。也許是從小父母對我就不怎麼關心吧,逃學打架基本男孩子做的事情我全都敢做,請家長是經常的事情,上初中之後我成了學校的混混頭,父母實在受不了,把我送到了天津的姥姥家,讓我在那裡上學。不在他們身邊又換了新地方,我不再打架斗毆出風頭,原來那麼做,僅僅是為了讓他們注意我還有這麼一個女兒,現在沒有必要了。我就在疼愛我的姥姥身邊自由自在的成長。父母來看我的次數越來越少,等我上高二時,那一年他們沒有來,我不想回去,我知道回去也是多餘的,他們還有弟弟。以後,他們每月寄來生活費給我和姥姥,算是不再來的補償吧?我不知道。
高三上學期,姥姥過世了,他們都來了,仿佛陌生人般的面對著,我打算留在這裡不再跟他們回家,他們沒有說什麼,留下一筆生活費,走了。其實我很想回去,就是已經不知道怎麼面對陌生的他們。之後我搬出去用他們的錢買了一間偏單——他們有的是錢,我要他們就給,以為這樣就能彌補我失去的東西吧,好笑。再以後,我考上了大學,他們給我開了一個戶頭,更省事了,有時要有大筆開銷時,我打電話,他們就會匯錢給我。很諷刺吧,我象是一筆固定的金錢流出,對於他們。
夢夢的自白(2)
當別人開始上網時我也買了一臺電腦,實在是無聊啊,遠離了家庭又不住校。
網絡是個好東西,它可以麻醉人讓人逃離現實、陶醉於虛幻的快樂中,象是吸食鴉片。知道那是不應該經常碰的,偏又忍受不住它的誘惑,不可救藥的沈迷其中,不想掙脫,就如此沈淪下去。
從大一開始,至今已三年,我唯一的網名便是『無色曇花』——夢是短暫的,曇花的生命僅有一現,蒼白的夢境中,一朵失了顏色的曇花悄然開放、凋謝,卻無人知曉。大一那年又一天我突然昏倒,去醫院檢查,是腦瘤。不知道是良性惡性,醫生建議我全面檢查定性治療,我卻只是笑笑,開了幾付藥離開——我已經習慣了被人忽視的感覺,這個社會的遺棄者,即使死了,也不會有任何人,流淚。我沒有告訴任何人,父母知道了也絲毫沒有用處,如果注定我要死去,告訴他們只會徒增他們的傷心——如果他們會傷心的話。我想在漸漸的心的背離之後,我不和他們聯系,他們會慢慢遺忘我的,原本人就是容易遺忘的動物。那麼當我死去,不知他們什麼時候纔會知道這個消息,我是不可能『親自』告訴他們了。
我不知曉自己還能活多久,過一天是一天吧,也許會一夢不醒,留在我營造的美妙世界裡,腐爛、發臭,漸漸成了白骨纔被人發現,到時候報紙的一個角落就會刊登出『某大學某女生死在家中xx天纔被發現。……由此可見社會冷漠到了什麼地步,我們應該……』而父母來認屍時回音我的腐爛氣味嚇得驚叫、面目扭曲……想到此處我就不禁冷笑,哈哈哈哈哈哈,真是好笑,他們會皺著眉與我凸起的眼睛相對,然後,一條蛆鑽出來嘲笑他們,那時候他們會怎樣啊,我狂笑笑得眼淚都出來了,真好笑啊!我很他們。
我又暈倒了,這次是在課上——大三開學以來我上的第一節課。昏迷在最後一排,當我清醒時,天已擦黑,6點多了,有4個多小時我失去了知覺,教室裡僅有幾個上自習的,和我同班的那些人早就無影無蹤。我的病加重了,昏迷的間隔越來越短。我起身離開,仿佛真的僅是做了一個夢。
就這麼慢慢死去吧,我不再吃藥,空虛的時候不是看書就是上網。龜縮在自己的小窩裡,這真的是我的外殼啊,久得已然忘記太陽的模樣,偶然出去,也是夜色一片。
(3)
我刻意逃離著人群,不願與人交往,卻無法阻止一些應該發生的事情——17歲以後開始有人追求我,不明白為何會看上我這種已經放棄自己的墮落者。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無情的拒絕,不留餘地。當我知道自己的病之後只能做得更徹底,不想欠別人也不想讓任何人為我傷心。我並非無情卻絕情,不僅僅因為我是沒有明天的人,對任何人來說,我是累贅。
開始有人說我是毒藥,愛上我的人毫無例外會中毒,在我無情的刺傷下,潰爛得體無完膚。
對於任何人,我僅是他們生命中的過客,他們僅是我的一場夢境,隨便就能捨棄,遺忘。除了自己我已經誰也不相信了,沒有朋友沒有敵人。我是毒藥,遠離一切,靠近我只有傷害。
(4)
對於網絡的虛幻,從頭到尾我沒有相信過誰見過誰,但我也不欺騙任何人,雖然不知道對方是否真實,我的真實別人也會懷疑,這都無所謂,誰認識誰呢。
那天一個陌生的名字陌生的人闖到我的oicq裡——『毒藥情人』。
『你為什麼那麼悲哀?』
我一愣,反問『怎麼?』
『夢中的曇花夢中的自憐,寂寞包圍著你,卻是無色的夢無色的花,無盡的懮愁。醒來之後你還擁有什麼?』
從來沒有人這樣說過我的名字,可能的確是如此,我下意識的回避了很多,其實我仍是渴望愛與被愛。
『我說中了。』
『……也許。』
『你生活在自己的夢境中麼?』
『是吧……』
『那麼你很漂亮了?』
『不』
『這樣的自憐自艾,不是美女就是丑八怪。』
『哦。』
『你很冷漠,很自私,我看你是丑八怪了。』
『是的』
『這樣說你都不生氣?』
『嗯。』
『奇怪的女孩兒,我喜歡你的個性。』
『哦。』
『你想認識我麼?我能夠讓你快樂,不再這麼懮郁。』
『不想,再見』
我關了Q走了,被他開始的話吸引,卻發現他原來和別人也沒什麼兩樣,無外乎是見面、上床之類。
『你好,奇怪的女孩,你不快樂吧?』他突然再次出現在陌生人欄裡。
『什麼叫快樂?』
『就是沒有不快樂。』
『什麼是不快樂?』
『你不開心、難過、迷茫、不知所措,鄙棄別人又被人鄙棄,你清高又希望能與別人交流,內心掙紮不堪……這就是不快樂』
我驚訝,沒有想過他會說出這樣的話,看他的資料:『真名:你去死生肖:空星座:空年齡:26畢業學校:打手中學工作:專業痞子自我介紹:我很帥我很壞,如果你是美女,就見面。千萬不要愛上我,否則你會死得很難看。——毒藥情人』
『你快樂麼?』
『我?快樂,每天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認識漂亮的女孩,尋找刺激,和哥們一起混。』
『這就是你的快樂?』
『當然,雖然庸俗,確是我得快樂。想必在你眼中我們這種人是社會垃圾。』
『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卻沒有資格去批評別人的生活。』
『哦?』『……咱們見面吧!』
『再見』
『哎,怎麼又再見?不想見就算了,不勉強你,接著聊聊。』
我沈默。
『走了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
我啞然失笑,『你不是毒藥麼?怎麼說我毒?』
『沒走啊?嘿嘿,名字是哥們送的』
『哦?』
『因為至今沒有女孩子能留得住我,我總是讓他們心碎。』
『哦。』
『你害怕嗎?』
『為什麼?』
『怕見到我就愛上我。』
『不可能』
『這麼乾脆,真不給面子。曾經有女孩子為我自殺。』
『死了麼?』
『死了一個,另外兩個活著。』
『厲害。你不覺的愧疚?』
『為什麼要愧疚?又不是我讓她自殺的,總不能為了別人勉強自己去接受吧?』
『……』
『雖然和我上過床,也不能意味著就代表什麼,我沒有強迫。』
『你……』
『不要說我不負責,這個社會有什麼責任是我這種人能承擔得起的?也許明天就在群歐中死去,說什麼未來。』
『那你為什麼招惹人家?』
『冤枉,是她喜歡我,我說過我的狀況,她還是追我,當時她有一點反對,我就不會繼續。』
『為什麼要這樣?』
『什麼?』
『要這樣做』
『……我是正常的男人,有寂寞迷茫混亂的時候,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不知道生存的意義是什麼,這樣能讓我快樂,證明我還活著。』
『……』也許他沒有錯,也許我們是一類的人——任性自私,為自己而活,卻背經離道,世人無法認同。我把他加為好友。
『該走了,下次再聊,你纔把我加為好友啊?夠狠心~』
『知足吧,算上你不到十個。』『走吧你。』
『哦?那我該放禮炮慶祝一番了。』
『諷刺?』
『實話,走了,約ppmm了,88』
我看著他最後一句話,哭笑不得。
(5)
時間仍在繼續,我的生活沒有多少變化。課去的越來越少,學校向我警告,我當作不知道。開除又能如何,也許沒等畢業我就死去,生命是自己的,不想不願浪費在學習上。我主動退學。建立沒有人反對,他們托人給我找工作,我拒絕了。於是錢照常寄來,不過多了些。於是我有足夠的時間去很多地方。雖然沒有什麼周游全國的願望,能去的地方我都去過了。
只有一次,我在海邊暈過去,醒來的時候,一彎新月斜斜掛在天際,海水蔓延在我腳下,一側身,一只小螃蟹橫行爬過,沙灘冷冷的,只有海浪的低吟。我失聲痛哭,沒有原因。
很久,『怎麼了?』我抬頭,關切的眼神、慈祥的面容,一對相攜散步的老夫婦關切的望著我,老奶奶將身上的衣服脫下給我披上,『孩子,有什麼事情我們能幫上忙嗎?』老先生溫和問著,我擦乾眼淚搖搖頭。衣服使我漸漸溫暖,『謝謝。』我哽咽著,他們沒有忽略我的存在。
他們對望,老奶奶輕嘆『孩子,你還年輕,這世上沒有什麼困難是無法克服的,想開些吧,有什麼事就和父母朋友說,別一個人悶在心裡。』我忍不住撲到奶奶的懷中大哭,她只是溫柔的抱著我,拍著我的後背,老先生遞過手帕。這個懷抱我等了十幾年,卻不是父母給的。那句謊話『我沒有父母』怎麼也說不出來了。正因為我深愛著我的父母,纔恨他們。
在他們家喝了熱熱的咖啡吃了一些糕點,我只是說和父母賭氣跑了出來,隱瞞了真實的情況。他們勸我回家,『世上沒有不愛自己兒女的父母。』這是老先生說的,也許吧,只是我父母的愛給了弟弟。
告別的時候他們將我送出很遠,等我回頭望--他們相攜而行,平淡而幸福,朝陽剛剛昇起,他們就迎著太陽而去,突然好羡慕、好感動。鼻子有些發酸,我揉了揉眼睛,向著他們的背影,微笑。
回到城市,仿佛美好的只是一個夢境,現實冷酷無情。在我旅行的這段日子裡沒有上網,原本以為網絡已融入我的生命,如今纔發現,只有在城市這個灰暗冷漠的地方,我纔需要網絡。我又龜縮到自己的殼裡,這趟出游耗費了近兩個月,我的體力透支得厲害,需要休息了。
屋裡一層灰塵,門縫裡塞了幾張收費單和廣告。恐怕除了水電廠煤氣站沒人記得我了。
(6)
網上的人陌生了很多,所有社區並沒有誰因為我的消失而詢問。Q上的朋友也只是互相招呼『好就不見了,還好嗎?』『一般,你呢?』『也行:)』……這些謊言,我暗暗咒罵,我快死了,一點都不好,卻仍說這謊言。誰會去真正關心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誰又在乎誰,說了又如何,最多得到的是不痛不癢的『安慰之詞』,可能會被人當成故事:我的一個網友快死了,是腦瘤。也可能轉身之間就忘記了,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永遠體會不了那種切膚之痛。
『小姑娘,你哪裡去了?』
『玩』
『去哪裡?一個多月沒見你了,想你』
『纔怪』不用看昵稱便知道是他了。
『真的真的,你這麼久沒來,我纔發現我喜歡你。』
『算了吧,你,我還不知道』
『不算不算。你知道我什麼啊?』
『你纔不可能真心喜歡上誰(除非是你命中注定的那個人),你最多是一時投入,過了便厭倦,遺忘了。』
『還是你了解我。你怎麼知道你不是我命中注定的那個人?』
『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不是我心中喜歡的。』
『真無情,我真的愛你啊。』
『我信麼?』
『……不信,你見我就信了。』
『算了吧。』
『又算。』
……糾纏不清,每次聊天都是這樣,有些厭煩,卻總覺得和他聊天是快樂的。他不太一樣,沒有問過我關於我現實的任何事情。
和他聊天仿佛漸漸變得必不可少。我知道他這種人要的我給我起,也知道愛上他是危險的事情。如果說我們都是毒藥,那麼我是烈性,發作快,立竿見影;而他卻是慢慢的腐蝕你的骨肉,不自覺中讓你中毒甚深,無藥可救。
『見面吧!見面吧!見面吧!!!』一上來的開場白嚇了我一跳。
『為什麼?』
『因為你的特殊,放過你或者當朋友太可惜了。』
『為什麼?』
『你不覺得雖然你我各走極端,但骨子裡卻是一種人嗎?』
『哪種?』
『一直寂寞著,卻渴望有人理解,哪怕是下地獄也有人陪伴身旁。』
『……』
『見面吧,我是認真的。』
『可我不是認真的。』
『為什麼?』
『不為什麼』
『給我一個理由!』
『需要理由麼?』
『你瞧不起我?還是自己丑怕見我?』
『都不是。』
『那是什麼?』
『不要逼我。』
『你還是看不起我?!』
『你認為身份背景重要麼?沒有誰瞧不起誰,只有自己瞧不起自己。不見你,如果你是認真的我不想傷害你;如果你不是認真的我不想傷害自己。』
『為什麼這麼說?我不會害你,我也不怕你傷害。』
『走了,再見』
『別走!說清楚』
『下次下次,你讓我考慮!』
『就是見個面,怕我吃了你啊?』
『下次再說,8888』我逃也似的關上了電腦,把自己拋入床上考慮這個問題。
見了面我們會發生什麼,我有這個預感,卻不敢仔細想,不想連累他,卻隱隱覺得該有一場戀愛了,如果就這樣死去,我不甘心。也許該去醫院確診到底還有多少時間了。
(7)
至多一年。當拿到這個結果時,我無聲笑了,這便足夠了。讓我自私些吧,不管別人,就揮霍著最後時光,更何況……也許他不會為我傷心,這樣我便沒有什麼牽掛了。
(8)
當我坐在『上古』酒吧裡,還有點不可思議,這便是約定的時間地點,就差那個人了,將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攪動著『毒之淚』我的衣著安靜與這裡格格不入——白衣黑裙,刺目而無力。在角落裡,冷冷看著那些快樂的孩子們,也許比我大,充斥著年輕人特有的狂傲浮躁。
有人拉開對面的椅子坐下,我抬頭——是目光深邃衣冠楚楚二十八九的男士,顯然不是我在等的人。『我可以坐下嗎?』『你已經坐下了。』『注意你很久了,這不是你這種女孩應該來的地方。』『也不是你該來的。』他微笑,『那一起出去走走吧?』我垂頭不再說話,注視著杯裡奇怪的慘蘭的液體,沒有勇氣去嘗試味道,僅僅是因為它的名字。
對面一陣騷動,緊接著一個低沈有力的聲音:『老兄,這不是你的位子。』人被拖離椅子的聲音。他來了。看表,遲到了3分鍾。亂亂的頭發不羈的眼神充斥著不屑,偏又含情脈脈——他有一對桃花眼。第一個人想表達一下他的憤慨,在看到他撕破的衣衫上面點點血跡,左臂上一道不淺的刀口流出的血時,就乖乖溜走了。
『坐』我指指翻倒的椅子。他一言不發坐在我身旁,腳架在了桌子上手搭上我的肩膀。『那邊。』
『這邊不是更好嗎?』他壞壞的笑,湊近我,熱氣噴在我的臉上,『像不像美女與野獸?』他回頭向後喊,『兄弟們?!』口哨聲響起,一片怪叫。『嘿嘿,不會嚇倒你吧?我剛打完架,就和兄弟們一起來了。』
我沒有回頭,直望著他『和我有關麼?你一身汗臭,建議你下次約人寧願遲到也要去洗澡。』
輪到他呆住了,皺這眉嗅了嗅自己『有嗎?……是有點……』
『坐到那邊去,如果你還想見到我。』
這回很聽話,他起身坐過去,他的弟兄們一陣口哨,他惡狠狠罵了一句。我喝了一口『毒之吻』,很辣,放下不再動它。
『你不害怕?你這種淑女怎麼會不害怕呢?!』他皺眉,腳又搭在桌子上,我盯著看沒回答。這次他自覺把腳放下去。
我掏了半天扯出一條手絹仍給他『我不想一會兒和死人說話。』
他笑了,痞痞的,晃動左臂『沒事,小意思。』卻還是拿手帕包紮了一下,後面又是怪笑。他伸手拿過桌上的牌號扔了過去,將他們轟走,頓時安靜了不少。
『你有什麼可嚇人的?』
『黑社會啊。』
『我早說了不怕。』
『在網上還當你是隨口說說呢,原來也有人這樣說,見了面還是怕的要死。』
我冷笑。
『喂,美女,一直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孟夢。』
『啥?夢夢?』
『姓孟,名夢。』
『好聽好聽,人如其名。』
我凝視著那杯雞尾酒。
『別不說話啊,乾坐著怪無趣的。對我印象怎麼樣?』
『還不錯。』
『我帥嗎?』
『算是。』
『我身體棒吧?』
望了眼他胳臂上的肌肉,『還不錯。』
『對我滿意嗎?』
『嗯。』
他又湊過來小聲說『那還等什麼?咱們上床吧?!』說罷他仰到椅子上放聲大笑。
我平靜的看著他『好。』笑聲猝然中斷,他張著嘴看我。『閉上嘴巴。很不好看。』他猛然合上嘴。『害怕了?』他搖頭。『對我滿意嗎?』
『滿意。』
『那為什麼反應這麼大?』
『我、我沒有想到,你這麼淑女竟然這麼回答。』
『我不是淑女,從來沒有承認過。』
『可是可是……』
『這身衣服是我所喜歡的,不要以為長裙長發就是淑女。』
『哦……』他的眼珠再轉,好像對剛纔丟面子很不甘心。『那你還是不是處女?』
『重要嗎?』
『當然,如果是,萬一以後你纏上我怎麼辦?』
『不會。』
『你不是?』
『是。』
『我的魅力可是無人能抵擋的,不信你整天和我接觸還捨得離開我。』
『一年,最多和你在一起一年。』
『不會吧?』
『長?那半年好了。』
『真不給面子,我一定要你愛上我。』
『你那麼自信?』
『當然!』
『賭?』
『賭!』
『你輸了找個貼著「治性病」的電線杆子大喊三聲「我的病有救了!」』
『你狠!你輸了……嗯~』他開始壞笑,『以後當我情婦,直到我厭倦了。』
『成交。』
『喂。』
『什麼?』
『你還沒有問我的名字。』
『對哦,你叫什麼?』
他翻白眼,『楊塵。』
『可惜了。』
『啥?』
『名字,詩意在你身上看不出來。』
他嗤之以鼻,『那玩藝能當飯吃能賺錢嗎?』
『……』
他端過『毒之淚』一飲而盡,『這是什麼?』
『酒。』
『我知道。什麼酒?』
『雞尾酒。』他大翻白眼,我忍不住笑了。『回答沒有錯誤啊。』
『什麼雞尾酒?不要告訴我是外國雞尾酒。』
『毒之淚。』
『好,以後喝這個,味道還不錯,就是淡了點。』
『走吧。』
『再見。』
『喂,是你和我一起走!』
『去哪?』
他抓住我的手,『make love~。』聽到的人開始竊笑。
我甩開他。『停——』
『怎麼?你答應的,不能反悔!』
『不是反悔,第一,你我纔是第一次見面,我不想這麼快。第二,我不希望你的血弄到我身上,』我指指他的左臂,血又滲出了,『第三~你一身汗臭,離我遠些!』
『這麼多規矩啊,真是麻煩。』他嘀咕。
我拍拍他的肩,『你再等等吧,兄弟。不行就先去找那些ppmm。走了,再見。』我走出門口。
『喂,就這麼走啊?我送你!』
我沒有回頭,擺了擺手,融入夜色中。
(9)
相見分離,多半都是在夜幕降臨,華燈初上,隱藏在黑暗之中,隨便一家酒吧喝著酒,相對無言或是聽他講打架的經歷。他很少問我的過去,我也沒有過去,正如沒有未來一樣,只是這麼活著。
至今為他裹傷口用去我九條手帕了,他打架的頻率不高,一、二周一次而已,但每次都會帶傷,我沒有勸阻過。與他相處自然而無優,不用擔心什麼,生命是自己負責的,無人能左右。有兩三次喝著酒我便突然暈過去,每次醒來身上都有他的衣衫,而他坐在對面,抽著煙,深深望住我,眼神中的憐惜疑惑與不安沒有掩飾,我從來不說原因,他也不問,僅僅是突然抱住我,很緊,我透不過來氣。他可能猜到了什麼,卻無法肯定。
在他狂放不羈的面具下面是沈默而悲哀的心。他打架、無所事事、上網見面,僅僅是為了不被那空虛的寂寞抓住,他逃離不去思考,因為脆弱而冷漠。當只有我們兩個的時候,他總是疲倦的枕著我的腿,如同孩子一般,仰望著城市之中僅有的幾顆星,看著看著,就這麼睡去。河東公園裡的長椅便成了我們夜晚的住處。
夢夢的自述(10)
農歷七月十四,鬼門開。寂靜的夜晚,在這繁華的樓群中一些人默默燒著紙錢,灰四下飄散,一種令人窒息恐懼的氣味便彌漫開來。
『你相信鬼麼?』
『不知道,在我沒有看到之前不會肯定它的存在。』
『據說,白天人看不見鬼,晚上鬼看不見人。』
『……』他樓緊我,『我想喝酒。』
『去哪裡?』
『我家有個吧臺。』
『走吧。』
第一次走進他租的小屋,不大,只有一間客廳加上9立方米多的臥室。很空曠,臥室裡只有一張床和立櫃。客廳裡則是一臺電腦,幾個軟墊,外加小小的吧臺,竟有不少酒。
『你不看電視麼?』
『無聊。』
我聳肩。
他敏捷地跳過去敲著酒杯『小姐,請問要點什麼?』
『毒之淚。你會配麼?』
他吐舌頭,『我只會把各種酒摻在一起。』
『那還是給我杯香檳。』
他遞過來,挨著我坐下。於是我們就在一盞昏暗的壁燈下默默喝著酒,看著窗外——盡管漆黑一片。
『我想……我這樣的人只能下地獄。』他低沈的聲音在空曠的房間內亂撞,我握住他的手,『那麼我也去。』他輕輕的吻我,『可以嗎?』我抱緊了他,杯子掉在了地上……
好寂寞阿……即使相擁在一起,也無法溫暖心底的涼意,在歡狂的最深處卻有想哭的衝動,不為了什麼,僅僅是兩個人更加寂寞了。汗在晚風中逐漸乾了,他的床好舒服、他的氣味好安全、他的懷抱好溫暖,我沈沈睡去。
醒來時天已大亮,他不在身旁。感覺疲乏得不想動,翻了個身便又滑入夢鄉。朦朧中有人在捏我的鼻子,很不情願的睜眼,他笑瞇瞇的坐在床邊,『很累吧?』我的臉頓時紅了,『嘿嘿,吃點東西補補。』他端過一個托盤,上面放著很多吃的。
『你做的?』
『是啊,嘗嘗,你有口福了,我還是頭一次做飯給不是我媽的女人。』
我微笑,『真的啊?好孩子。』
『你佔我便宜啊?快趁熱吃吧。』
『我穿衣服,你先出去一下。』
『喂,還害羞啊?我就在這裡看著你換。』
『去去去去!』我拿枕頭丟他,他笑嘻嘻的跑走了。
(11)
之後,我就和他住在一起。他不在的時候我便寫下我們之間的點點滴滴,我的記憶好像在逐漸衰退,精神無法集中,思維飄忽不定,常常幾天幾天頭痛的睡不著覺。我知道,時間不多了,要抓緊做一些事情。我不想死在他的面前,不想看到他的眼淚,我真的,愛上他了,雖然我從未對他說過。
他察覺到什麼,總是要帶我去醫院,不再讓我喝酒熬夜,越來越溫柔,雖然他也沒有對我說過什麼,但我明白他的心意。
冬天裡的第一場雪就這麼落下了,很大,滿天鵝毛飛舞,在這孤獨的城市中很少能夠看到這景色了,那天農歷臘月初七,我的生日。他不知道。我已經23歲了,不能算夭折。春節他想帶我去見他父母,我不知道是否還能夠活到那個時候。
(12)
那天我醒得很早,五點多,外面漆黑一片,他還在熟睡,我輕輕吻他如同純真大孩子的臉龐,淚滑落在他的臉上。
帶著提前收拾好的行李,我獨自上路。
不知道何去何從,卻清楚不會留在這裡,不會再回來。天很冷很陰,沒有風,我就這麼離開生活了近十年的城市,義無反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