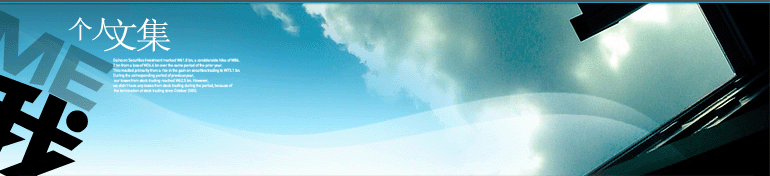|
引子
高樓林立,車輛穿梭,霓虹閃爍。
這座城市繁華如斯。
如果你的外表一如城市那般光鮮,如果你總是出車入輦,華衣美食,那麼,你永遠不會知道,在那些高樓大廈的後面,有一個叫老鼠街的地方;你也不會知道,在那條街道上,曾經住著三個少年。你不會注意他們,正如你從不去注意陰溝裡活著的老鼠。
你能不能告訴我什麼是人性?這對我敘述他們的故事很重要。
他們最卑微同時也最高貴的活著,或者死去。
而我面對他們,自慚形穢。
老鼠街人人都活得像老鼠,因為這條街是這座大城市裡最窮、最破爛、最骯髒的地方。老鼠街裡的人只出不進。很少有人來這裡,不,是幾乎沒人願意來這裡。
其實老鼠街是很善良大方的。它非常樂意接納成群入駐的老鼠,以及像老鼠那樣活著的『人』——我是其中一個。
我沒有名字。別人都叫我『刀疤鼠』,因為我額頭上有道疤。開始是頭兒這麼喊我,後來全街人都這麼喊。
除了我的兩個兄弟,還有我家隔壁的傻妞。他們叫我老大,傻妞也跟著我叫。叫得我心頭熱熱的。
我是老大。我在老鼠街有個家。我們家最窮,最破爛,就連老鼠也看不起。可我是家裡的老大。
做老大,就得有老大的責任。老鼠也要生存。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這句話是我們頭兒最常掛在嘴邊的。鬼知道他從哪兒聽來了這句話。總之,我覺得這話真他媽的有理。頭兒很少有話能讓我記住,除了這句。老鼠街有自己的江湖,江湖之外有更大的江湖。我是江湖的一分子。江湖的生存方式是打殺。
扛把砍刀,跟在一群嘍羅們後面,為某個地盤跟別的幫派的人進行一場械斗。有人死,有人活。然後頭兒派給我們一些辛苦錢。
我得到的錢總是不多,因為有人告訴頭兒我打架時不夠盡心盡力。頭兒沒趕我走,對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我要活著。每天我要活著回家看到我兩個兄弟。他們叫我老大。老大不能死,老大死了沒人養活他們。
我不願意我的兄弟插手江湖。他們不能。
老二常常對我說老大我是不是很沒用我什麼也做不了。我說不,在我眼中老二你比誰都強。老二的眼神看上去空洞而蒼白,三年來他日復一日的搬把凳子坐在街口等人。等誰我不知道,老二自己也不知道。老二說那個人一定會來。老天這麼告訴他的,老天不會騙他。老鼠街的人嘲笑老二,叫他『白癡』,因為三年來老鼠街一個陌生人的影子都沒有。老二一直在等,風雨不改。我相信老二,說不上原因。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沒有原因可言的。有的人生來要流浪,有的人生來要痛苦。老三要等人,沒有原因,那就讓他等好了。
看到老三的時候我總會莫名的心疼。我們在一起多久了?大概有10年了吧。這十年裡老三說過的話不超過十句;十年裡我只看見老三笑過一次,那是三年前我們跟老二結拜的時候。我每次回家,總是看見他沈默的坐在陰影裡,目光凝滯。有時候我半夜醒來,發現老三定定的看著我,然而黑暗裡我看不清他的眼神。
我對老三了解的太少。
以前我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活在這個世界上,後來想通了:我的命不是自己的。上天安排我為我的兩個兄弟、為我們三而活。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是否會分開。這個問題太遙遠。
未來是無法讓人預測的。像我們這種人,要避免恐慌,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也不想。
有一天我回家後發現屋子裡多了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我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女人。她很年輕,最多21歲;她穿著一身火紅的裙子,就像一團火似的燃燒著這間屋子。看到她眼睛的時候我知道我陷進去了,萬劫不復。這個女人是我命定的克星,我只能這麼說。
老二在一旁低聲道老大這就是我等來的人,她叫幸子。
幸子走過來,眼睛裡盛滿濃濃的笑。她說你就是老大嗎?老大你願意我住在你家裡嗎?
當然!我幾乎是脫口而出。
老三驚詫的看著我,而我無法作出解釋。我隱隱地感到自己似乎犯下一個極大的錯誤。
叫幸子的女人在我們屋子裡住下了。一張木板加一條毯子搭成了她的床。
她為什麼會來老鼠街?為什麼要住到我們家?老二是怎麼遇到她的?我既想知道,又不願知道答案。
有些問題是不需要問,也不需要答案的。存在的本身就是答案。
就像我跟老二、老三之間,從來都沒有問起過什麼。我們活在一起,這就夠了。
幸子到來的第一個月生活還是平靜的,好像沒有任何改變。其實要說改變,也有,就是我每天會多帶一點吃的回來。幸子總是穿著一身火紅的衣服,早出晚歸。我逐漸習慣了這樣的日子。
那天晚上,天氣燥熱不堪,我怎麼也睡不著,就一直處於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狀態。迷迷糊糊中,聽到屋角傳來嘩嘩的澆水聲。我尋聲望去,看到一具象牙般白的、在黑暗中幽幽泛光的胴體——幸子正在洗澡。
她面向牆壁,不知道我在看她。大概她以為我們三兄弟都已經睡的很沈了吧。
我咬著自己的胳膊,努力不自己發出聲音。幸子洗完澡,上床睡覺。我感到她有意無意的朝我這邊望了一下,忙閉上眼,翻過身去,纔發現身下的床褥,不知何時已濕了一片。
第二天,我回家後發現幸子的床前多了一道簾子。不知是從哪裡找到的一塊破布,卻具備了牆壁的功用。
從那天起,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渴望回家,而又更害怕回家。
有時候我會發呆,更多的時候我只是在老鼠街附近四處晃蕩。
那天我鬼使神差的買了一只脣膏。紅紅的,配她的衣服。
遠遠地,看見她站在屋前,燦若紅霞。
我說:給。
她接過脣膏,臉上浮起不可琢磨的的笑意。然後她看著我說,老大,你今天沒有帶食物回來,老二、老三要挨餓了。頓了頓,又指著那只脣膏說:你是從地攤買來的,對吧?
我僵住,說不出話來。
她說老大你知道嗎,你帶回來的那些食物都是狗食,我從來不吃的,全扔掉了。
她說老大喜歡像我這樣的女人是需要本錢的。
她說老大你看看我這一身打扮——你一輩子都買不起。
末了,她轉過身,低聲說老大你根本不用討好我。你不會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那支脣膏,劃出一道美麗的拋物線後,摔進陰溝裡。
我站著,仍舊說不出話來。
剎那間我明白了,我要做的是什麼。
我算什麼呢?我連自己兄弟的嘴巴都糊不飽,我連一個合格的混混都算不上,只是一只老鼠般的活物罷了。
我記得頭兒說過,我還沒有真正混入江湖。
下一次幫派爭斗中,我砍斷了對方一個嘍羅的胳膊。他的血濺了我一臉。血的味道是很腥臭的,但是很艷麗,很奪目,漫天的紅,像幸子的裙子。我一下子喜歡上這種感覺。
頭兒很高興,誇獎了我一番,賞給我一筆我從未見過的大數目的錢。
我跑到城裡最大的商場,用那筆錢買了一支最貴的脣膏。我把它丟在幸子床上。
我發現要掙錢其實很容易,只要你肯把命豁出去。
我見到越來越多的血,頭兒給我的錢也越來越多,我給幸子買的衣服和化妝品也越來越多。
看到女人穿著自己掙錢買來的衣服,這種感覺是很不錯的。
那天,我買了一條鑲著鑽石的項鏈。回到家時,幸子已經睡著了。我把她放在幸子的枕頭邊。
半夜裡,我在夢中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在我臉上移動。睜開眼,是幸子。
她撫著我的臉,叫:老大,你過來。
我就過去,跟著她坐到她簡陋的床上。
她褪去衣服,露出象牙般光潔的胴體。
我19歲了,從未碰過女人。
她撫平我的顫抖,引導我進入她的身體。
在我全身僵直懸於一線的剎那,我聽見她呼喚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名字:陳樹,陳樹。
陳樹是誰?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願去想。
我此時只有一個念頭:這個女人,她終於屬於我了。
老二、老三他們,也該有個嫂子。原先只有男人的屋子只能叫做屋子;有了女人,纔能稱得上是家。
但是,老二和老三的眼神中,卻有了越來越多我看不懂的東西。老二不再去街上等人,總是低著頭喃喃自語,我叫他,他半天也沒反應。老三以前喜歡枕著我的胳膊睡覺,現在也不了。有時候他明明在看著我,當我直視他的眼睛時,他卻飛快的把目光逃了開去。
我只有在心裡默念:老二、老三,我會讓你們幸福。很快,很快我們就都會幸福了。
某天,傻妞突然跑過來對我說:老大,你是不是很喜歡那個叫幸子的女人?
我說是的,我很喜歡她。
傻妞說你能不喜歡她嗎?
我笑了一下,說,不可能的。傻妞你還是個孩子,你不會懂。
傻妞的臉就變的很懮傷。我從未想到傻妞臉上還會有這種表情。
為什麼一切都開始變了呢?
還是,變的其實只有我自己而已?
有一點我很清楚,那就是我們再也回不到從前了。
也許只要擁有現在就夠了。
我相信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命定的軌跡運行的,我只要安心的走下去就行了。這是一種簡單而行之有效的生存方式。
幸子到來的第三個月我開始做一個很奇怪的夢:在無邊無際的紅色中,一只烏鴉衝我無聲的叫喊。
我不知道這預兆著什麼。有人告訴我,紅色代表幸福,烏鴉表示災禍。也有人告訴我,夢總是與現實相反。
這個夢持續一星期後消失了。
再半個月後的一天,我回家,老二、老三像往常一樣在等著我。
環顧四周,總覺得屋子裡少了點什麼。
我問:幸子呢?
老三緩慢的站起身,揭開他床上的被子。
我看見幸子很甜美很安詳的睡著,臉上還帶著笑容。
我喚她:幸子,幸子!沒有回應。睡夢中的幸子聽不到我說話。
我笑了,走過去,想搖醒她。
可幸子永遠不會醒來了——她的脖子上有道細細的傷口,暗紅色的血液凝結在那裡。
她死了。
我的笑容霎時凝固。如墜冰窟。
原來一件美麗事物的毀滅是這麼快。你永遠不會有准備的時間。
我的身體順著床沿滑到地上。
老三試圖把我拉起,我用胳膊阻住他。
誰乾的?我問。
老三張了張口,喉嚨裡發出嘶啞的聲音。
老二站了起來,說:老大,幸子是我殺的。
我沒有抬頭,目光瞄向屋角的那把砍刀。你再說一遍!
老二說老大你忘了嗎?幸子是我帶回來的女人。她不屬於你。
老二之後還說了什麼我已經記不清了。
我突然明白了三個月前我犯下的錯誤是什麼。我想笑。
殺幸子的凶手是誰並不重要。
沒有將來,只有發生的事實。事實沒得選擇,只有選擇接受。幸子死了,這就是事實。
夜很深,老二、老三的眼睛漸漸合上。
世界像陷入黑白的電影裡。
我看見一只烏鴉飛過來,在窗口無聲的叫喊。
天快亮了。奇怪!我第一次思考這個問題:天為什麼要亮呢?就這麼一直黑著多好。天一直這麼黑著的話,就什麼也不會改變。
可是天就要亮了。
三個月前的老鼠街沒有幸子,我們三兄弟生活的很好,從來不覺得缺少什麼。
現在這個女人死了,我們三人還活著。
我得到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呢?
我想不明白。那就不要想。
老鼠街也不再是從前的老鼠街了。
我背起幸子。她的身體冰涼。
等太陽昇起,她的身體就會變溫暖的。
我看了看老二和老三,他們在幸福的微笑。
然後,我輕輕的離開。
幸福的路好象要走好遠。我不看路,我只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