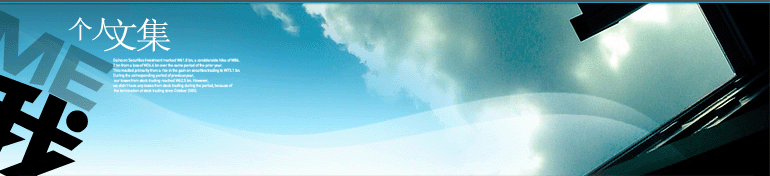|
沒有所謂尖銳、疼痛的青春,有的只是一敗涂地。
(1)
『雲寧,你真的很白癡,』遠夏搖晃著頭說,『這道三角函數題我至少跟你講過一百遍了,你竟然還不會!』
『是的,我就是白癡。』我毫不否認。『你是大天纔又怎麼樣?誰叫你是我哥哥的?你就得管我!』
遠夏小聲嘟囔:『偏不管你,小丫頭片子。』
我聽見了,馬上大聲還擊:『你敢?!老男人片子!』
這時姑姑的聲音就會從隔壁傳來:『遠夏,這麼大了還不懂事,跟妹妹爭什麼呢?』
『沒什麼,鬧著玩呢!』遠夏心虛地回答,然後把練習本推到我面前,惡狠狠地道:『白癡,重做!』
(2)
『你怎麼說普通話?』在這個南方城市,幾乎每個初次和我碰面的人都會這麼問我。
『因為我在北方呆過幾年。』我平靜地回答。
『那你會說本地話嗎?』
『不會。』
『唉呀!』她們無一例外會嘆息一聲,拿一樣的眼光瞅我,好象我身上缺胳膊少腿似的。
只有一個叫明熙的男孩,過來對我說:『雲寧,你可不可以教我說普通話?』明熙有著很大很明亮的眼睛,睫毛濃密得讓女孩們妒忌。
我只對他說了三個字:『別煩我。』天生對這種看上去乖巧、討老師喜歡的學生反感。
明熙遠遠走開,臉上沒有表情。
但是班主任偏偏安排我與他同桌。
(3)
給遠夏寫信:『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寫了滿滿三頁紙,然後撕碎,扔進垃圾簍裡。
我找不到更多的詞語可以寫。
這裡,不會有人叫我『白癡』。
(4)
我試著融入這個城市。
地理書上說,這裡的氣候很好。沒有北方冬春肆虐的沙塵暴,沒有深及膝蓋的大雪。空氣濕潤而曖昧, 像一壺溫吞吞的永遠燒不開的水。
這是我曾經生活過九年的家鄉。曾經而已。對這裡的人來說我是個異鄉人。在北方的時候別人也認為如此。
我一直是沒有家的人。
(5)
與全班男生為敵。
已經習以為常。從小學到初中,都是這樣子。
放學時開始吵。七個男生對我一個。
他們都纔十三、四歲的年紀,罵出來的話絲毫不比成人遜色,句句都設計到人的生殖器。
我只不停的重復:『卑鄙無恥下流骯髒齷齪``````』似乎在作無用功。
他們開始推我、搡我,幾個人堵住我不讓我躲閃。
我從牙縫裡擠出幾個字:『我看不起你們!你們不配和我說話!』
我的眼鏡被踩成粉碎,書包從四樓扔了下去。
他們一哄而散。
我趴在座位上低聲叫:『哥哥,哥哥,哥哥`````』眼淚不受控制的往下掉。我變得懦弱了,以前我是絕對不會因為這個哭的。
暮色四合,想起校門將閉。抬頭,看見書包擱在講臺上,乖乖巧巧的樣子。
窗外有人影閃過。心中一動。
但那不會是遠夏,不會是我哥哥。
(6)
喜歡金庸、古龍、黃易;喜歡『仙劍』、『星際』、『拳皇』;喜歡《青春》《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喜歡著這些和我外表看上去極不相符的東西。
因為它們都是遠夏喜歡的。
十三歲那年,遠夏問我:『雲寧,想不想跟我學吉他?』
『當然想!』我答。事實上,這句話我已夢寐以求了四年。
『學吉他很苦哦,要把手指頭磨出繭來。』他伸出手掌,給我看那上面厚厚的繭。
『我不怕,』我說,『你一定要教我,不許反悔。』
遠夏沒有反悔,我也沒有學會吉他。
那個噩夢般的夏天,我不得不離開北方,離開遠夏。
媽媽一直不明白我為什麼要花三年時間纏著她給我買吉他,因為我一點音樂細胞都沒有。
高中的時候,吉他終於買來了,卻從來不彈。
它立在電視機旁,應該不會寂寞。
(7)
開始把自己打扮得像個男孩子。
頭發理成板寸,穿很寬大的滑板服,管幾個女生叫老婆。
『雲寧,你是不是變態?』
『呵呵,我是同性戀。』我很認真的告訴他。
於是我在校園內開始大大的有名。
不少人在我背後指指點點。我把頭揚得更高。
有男生試探地邀我去打電游。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出來時我堅持付錢。
當初那幾個圍攻我的男生也頻繁地來邀我。每次都很爽快地答應了。當然,結帳的時候一樣很爽快。
我只玩『拳皇』。不停地找人單挑,不停地輸。到後來幾乎沒人願意和我對打了。
除了一個叫何宵的男子。
之所以叫他『男子』,是因為不知該稱他『男孩』還是『男人』。每個周末我都會在電游室碰見他。
他留著很長的碎發,劉海垂下來遮出眼睛。左耳戴著一只銀質耳環。皮膚很白,看上去乾乾淨淨的樣子。從他的外表我猜不出他的年齡。
男生們指點我去找他。因為他是這一帶玩『拳皇』最厲害的人。
我把一張百元鈔票擺在他面前:『喂,你教我玩。』
他連頭都未抬,專心致志地盯著屏幕:『小女娃,不要這麼「猛」。』
『我想讓你教我,』我生硬地說,『拳皇。』
他把鈔票丟給我:『女娃子不適合玩這個。過家家去吧。』
『我不是女娃子!』
他終於抬起頭,乜斜著眼,臉露譏嘲的笑容:『那你是什麼?』
『你管不著!』
『聽說你是個同性戀?』他臉上的笑容更深。
我憤怒地瞪著他,一言不發。
然後他俯身湊在我耳邊輕聲說:『告訴你,我也是。』
(8)
轉學半年後在親戚家裡聽到了遠夏結婚的消息。據說婚禮辦得很豪華,很熱鬧。
那天我在電游呆了一整晚,瘋狂地玩『拳皇』,手掌被操縱杆磨出血。
何宵給我手上纏了一圈又一圈的衛生紙,邊纏邊說:『你忍著點。這麼晚了沒地方給你買創可貼去。』完了他問我:『你今天是不是受什麼刺激了?』
我避開他的眼睛:『怎麼可能?考試沒考好,不想回家聽老媽嘮叨。』
『是嗎?』他臉上又露出譏嘲的笑容:『我沒想到你還在乎成績。』
『你沒想到的事情還多著呢!』我不客氣地頂了一句。他扭過頭繼續在街機上『奮戰』,不再理我。
偌大的電游室裡只剩下我跟何宵兩個人。老板在吧臺後面昏昏欲睡。
忽然感到渾身發冷。
『何宵!』我叫著他的名字。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他硬邦邦地道。
『你做我哥哥吧。』
他背對著我。空氣裡除了沈默還是沈默。街機發出古怪的聲響。
『你聾了嗎?』我一錘子砸到他肩膀上。『你說話呀!』
『你害我GAME OVER了。』何宵轉過身來,似笑非笑:『我正在考慮該叫你「妹妹」還是「弟弟」呢。』
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死。
(9)
十三歲之前我只有一個哥哥,他叫遠夏。他現在與我毫無關系。
十四歲之後我有了一個哥哥了,他叫何宵。至少目前他與我關系很『鐵』。
但是,以後呢?
(10)
回到學校,已經過了早自習的時間。
明熙小心翼翼地問我:『昨天晚上你上哪兒了?』
我厭惡地橫了他一眼:『不乾你事!』
『班主任早上在班裡挨個盤問呢。』明熙小聲說。『我跟老師講你回親戚家了。呆會兒老師問起你,你就這樣講,啊?』
『謝你好意,』我說,『以後請不要多事!』
『聶雲寧,』班主任走進教室,像貓逮到耗子那樣盯著我,『你媽媽大電話告訴我說你昨天一夜沒回家。你乾什麼去了?』
『沒什麼,老師!』我站得筆直,很大聲地回答道:『我打游戲機去了。』
我看見明熙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
(11)
不管在哪裡,我都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
班主任把明熙和我調開,理由是『明熙原本是個很誠實的孩子,跟你坐在一起後就學會謊。』真是可笑,一學期裡我跟他說話總共不超過十句。但是『罪名成立』,我坐在了教室的最後一排。
母親對我說:『你為什麼要回來?你呆在你姑姑家不好嗎?你自己不檢點也就罷了,不要讓我跟著丟臉!』
是的,我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回來?為什麼要回來?
(12)
『啪!』遠夏的手掌響亮地扇在我臉上。
『雲寧,你回去吧!這兒容不下你。』遠夏的臉上寫滿失望。『你簡直是無藥可救!』
我最愛的哥哥打了我。他根本就不願聽我一聲辯解。我站在那裡,渾身顫抖,眼睜睜地看著他把門衝我重重關上。
可是哥哥,我真的沒有撒謊。
可是哥哥,我真的沒有撒謊。
可是哥哥,我真的沒有撒謊``````
(13)
走進教師,看見桌子上躺著一張卡片:
明天是我15歲生日,來我家參加我的生日PARTY好嗎?
明熙
抬頭四顧,發現班上幾乎每個人都收到這種卡片。
我把卡片攥在手裡三秒鍾,然後機械地撕成碎末,衝進下水道裡。
兩天後在走廊裡碰到明熙。
『雲寧,你昨天怎麼沒來?——你收到我的請柬了嗎?』他開口問道。
『沒有——我不知道什麼請柬。』我回答,頭也不回地走進教室。
忽然覺得自己真他媽的賤。
(14)
遠夏已經有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我對此不感到驚訝。如果說有,也只是驚訝於自己的平靜。
『哥哥,恭喜你了。』我在電話裡說。
『是雲寧啊,』遠夏的聲音依然悠揚悅耳。『好久不見,怎麼一直都不打電話過來啊。是不是把哥哥忘了?』
『怎麼會呢,哥?』我答:『小外甥可愛吧?』
『是啊,很可愛!你呢?你過得好嗎?』
『很好。恩``````我嫂子怎麼樣?』
『她也很好。』
``````
『沒什麼事就掛了吧,』他說,『別浪費電話費。』
『哦,好。再見,哥哥。』
『再見。』
聽筒裡傳來『啪嗒』一聲,接著是斷斷續續的『嘟嘟』聲。
我握著聽筒,想哭又想笑,
我們都表現得好象什麼也沒發生過。
是不是真的什麼都沒發生過?
(15)
明熙轉走了。這件事在班上並未引起半點波瀾。他本來就是那樣平淡無奇的一個人。
只有班主任不無遺憾地說了句:『該走的不走。』她的眼光停在我身上。
我裝做沒有聽見,若無其事地低頭看小說。
只是有一天,當我無意間回頭望見那張挪到我後面的空蕩蕩的桌子時,心裡突然湧起一陣難過。
那個睫毛很長,眼睛很亮的男孩子,我還欠他一句:『對不起!』
(16)
『雲寧,你就要初中畢業了吧?——以後不要再到這裡來了。』何宵對我說。
我盯著屏幕:『你也在乎這個嗎?』
『恩。』他用少有的肯定語氣回答:『我最近也不會來——馬上就要高考了。』
我轉過身,疑惑地望著他。
『奇怪嗎?』他自嘲道,『我已經是兩屆的「高四生」了。』
(17)
我上了一所二流高中。似乎一切都順理成章。
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到何宵。聽別人說他去了北方的一所大學。
這是我纔發現除了知道他叫何宵外,其餘的一無所知。
我叫了他整整一年『哥哥』。
以後我再也沒去過那家電游室。
(18)
班上竟然還有一個說普通話的人,並且比我說得還標准。他叫沈言,是地道的北方人。
『世上哪有那麼多同性戀的人?』人群中,沈言的聲音尖銳地刺入我的耳朵。
我提著一袋面包,笑容滿面地對一個女生說:『親愛的,我給你帶早飯來了。』
(19)
班級聯歡晚會上,沈言帶了一把吉他來。
他唱:『我只能一再地,請你相信我,那曾經愛過你的人,那就是我``````』
——《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猝不及防地淚流滿面。
(20)
『我只能一再地,請你相信我,那曾經愛過你的人,那就是我``````』遠夏的聲音有如天籟。
這首歌,我如癡如醉地聽了四年。
最後一年,是站在遠夏的房間外面,聽他彈給他的女朋友聽。
我曾在遠夏門外怎樣的流淚,遠夏永遠不會知道。
我知識他不聽話的、逐漸變壞的妹妹。
我的改變讓所有人大吃一驚。我走進教師的時候,全班每個人都注意到我腦後紮起一條單薄得可笑的辮子。
沈言在路上攔住我,眼裡盛著濃濃的笑意。
『你准備做個正常人了嗎?』他問。
『我從來就沒有不正常!』我反駁。
『是嗎?』他勾起嘴角,『——我還以為你是為我改變呢!』
『你可真是會做夢。』我譏誚道。
『那天我看見你哭了,』他似乎是漫不經心地說道,『你不必對我隱瞞什麼。』
(12)
想起已經很久沒玩過『拳皇』。
無意識地逛到一家電游室前。正是生意最好的時段,不時有人進進出出,嘈雜的聲音隔了很遠也能聽見。
一幫男孩子從裡面出來,邊走邊談論剛纔的戰績:『手真臭,以後再不玩拳皇了。』
我笑笑,想當初從何宵那裡學來的一手絕技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那個叫『何宵』的男子,再不會出現在這裡。
然後左手腕莫名地痛。
『你手腕上那條疤是怎麼來的?』何宵有一次問我。
『小時侯爬樹刮傷的。』我答。
這理由很合理,何宵絲毫沒有懷疑,連我自己都快信以為真。
那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對著淺淺的血痕無聲痛哭——當她拿起刀片割向手腕時,竟然搞不清血管在哪裡。
遠夏說得很對,我真的是個白癡。
(23)
『你可不可以做我哥哥?』我對沈言問了一個很快讓我後悔不迭的問題。
『我不需要妹妹!』他斷然否決。『對我來說,異性只分兩種:女朋友和陌生人。沒有第三種可能。』
『我``````不可能會喜歡上你的。』
『你考慮清楚,』他說,『你對我感興趣——我看得出來。』
『不是你想的那樣``````』我有氣無力地回答。
(24)
終於還是決定去找沈言,但是到處都看不到他人影。
『他在小樹林那邊練琴。』有人告訴我,臉上帶著幸災樂禍的表情。
我沒有在意。我只有一個念頭:趕快找到沈言。我好不容易纔下定決心。我怕我下一秒鍾就沒有勇氣說出口。
迎接我的,是一對糾纏在一起的軀體:沈言正和一個女生忘情地擁吻。
我的大腦剎那間一片空白。『逃呀!』一個聲音對我說。我用比來時快一百倍的速度逃離此地,不停的跑,直到雙腿失去知覺。
眼前又出現世間最丑惡的一幕:兩具赤裸的身體糾纏在一起翻滾——是姑父和一個陌生女人。
那個夏天,姑姑出外度假。
惡心,極度的惡心,我開始嘔吐,想要把五髒六腑都吐出來。
『哥哥,姑父他``````他是個壞人!』
『他罵你了還是打你了?』遠夏說,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
『哥哥``````姑父他嫖娼。』
『雲寧,你胡說些什麼?』遠夏滿臉厭惡,『你怎麼變得這麼不招人喜歡?』
『哥哥``````』
『我警告你,雲寧,你再這樣無中生有就別想呆在這裡!』
好的,哥哥,只要你肯讓我留在你身邊,只要你能分給我無論多微小的愛,我可以什麼都不說,什麼都忍受,哪怕深厚總有一雙骯髒的、窺視我的眼睛,哪怕我整整一個夏天,洗澡都不敢脫衣服。
(25)
再見到沈言,我表現得若無其事。
這個講普通話、會唱《流浪歌手的情人》的男生,他不可能會成為我哥哥。他只是個陌生人。
想起他的那句『名言』,覺得由我來用也很合適:對我來說,異性只分兩種:哥哥和陌生人。沒有第三種可能。
(26)
高中過去一半。無悲無喜的生活。
遠遠地,看見一個熟悉的人影,斜倚著欄杆。
『哥哥!』我大叫,朝他直奔過去。他望著我,笑容如清澈藍天。
『哥哥,真的是你!』我抓住他的手,確定眼前這個人真真切切的存在。
『我還能有人仿冒麼?』叫何宵的男子說。
我們找了一間小酒吧。
『你怎麼會突然來看我?你不是在北方嗎?』
『我早就回來了。事實上,我在那邊只呆了兩三個月。』
『為什麼?』
『我不適合北方。』他笑起來,『當然,最主要的是——想你了!』
『哥!』我有些惱火,『不要拿我開玩笑!我要你說實話。』
他苦笑了一下。『說什麼呢?我從來就沒喜歡過北方。雲寧,我去那裡,只是想知道那兒究竟有什麼東西值得你牽腸掛肚。可終究還是被那邊的沙塵暴趕了回來——很沒用,是不是?』
『哥哥``````』鼻子發酸,可是流不出眼淚。
『後來我就去了南邊,那個如暴發戶般崛起的城市。其實我想去的地方一直是那裡的一所美院,可是花了三年時間都沒有進去——我總以為我不會被第一志願錄取,但偏偏``````』他停了下來,伸手倒酒。
『雲寧,你戀著北方;而我,只能屬於南方。』何宵的聲音,疲憊而悲哀。
(27)
桌子上躺著一封信,字跡陌生。
『``````你一定不記得我是誰。初中時那個有幸與你同桌半年的男生,此刻懷著深深的愧疚之心寫信給你``````』
『``````看到你被人欺負而無法施以援手,是我人生最大的失敗``````』
『``````尤其不能讓我原諒自己的是,由於我的疏忽,全班就只有你沒來參加我的生日聚會。那件事給你帶來很大的傷害吧``````』
『我的18歲生日就要到了,這次你能來嗎?』
看到署名:明熙。
那個單純如斯的男孩子,我連他的面孔都已記不清。
信封上沒有留地址。
很想為自己的初中大哭一場。
(28)
『雲寧,你變了這麼多。』何宵指著我長以及肩的頭發,溫和地笑,『是為某個男孩留的嗎?』
『永遠不會有那個男孩的。』我答。
『不要說得這麼絕對,雲寧。』他瞇起眼睛。『你根本就不是同性戀``````』
『你``````』我又驚又怒,像刺蝟突然被拔光了所有的刺。
『從第一眼看到你開始,我就知道。』
『是嗎?』我努力使自己平靜下來。
『是的,』他繼續說道,『當然,我也不是你的「同類」。當初之所以那麼說,是因為不想當你花錢買來教你玩游戲的「工具」。』他頓了頓,『可也沒想到會當了你的哥哥。』
他直視著我的眼睛:『雲寧,你想聽真話嗎?其實我——』
『不,哥哥,請你不要說,』我驚惶失措地打斷他,『我知道,你一說出來,我就沒辦法喜歡你了,一切就都完了。真的,哥哥,求你不要說好嗎?』
他一動不動,眼裡的光亮一點一點地退色。最後他輕輕地答道:『好的,雲寧,我答應你,我不說。』
(29)
左手腕又在隱隱地痛。
遠夏的歌聲那麼遙遠。
他訂婚了,幸福的那個女子是我的小學老師。我站在遠處觀望,用力咬住自己的手腕——那道傷口還沒有愈合。
他們相識於一次家長會。遠夏找她詢問我為什麼老是被班上的男生打得傷痕累累。
如果,我一直是個好孩子。
只是如果。
從此再沒有一絲一毫屬於我的幸福。
訂婚典禮後,我明白,我成為這裡最多餘的人。
『遠夏還沒有教我吉他。』我對自己說。『他不可以反悔。』
但這條借口是多麼不堪一擊。
(30)
『哥哥,我們認識四年了吧?』我對何宵說。
『是啊。』
『那哥哥,你很快會厭煩我的。』
『豬頭,怎麼會呢!』何宵敲了敲我的額頭。『你太愛胡思亂想了。』
哥哥,我們能永遠這樣子對不對?永遠這樣子``````
(31)
給遠夏打電話。
『哥哥嗎?我是雲寧。』
『哦,雲寧,是你啊。你過的怎麼樣啊?』
『還好。你呢?』
『也還好,就是忙得不可開交。』
『這樣,代我向嫂子問個好。對了,小外甥會說話了嗎?』
『雲寧,你記性怎麼差?』遠夏在電話那頭哈哈笑道:『他都三歲多了,上幼兒園呢!』
就在那一剎那,我清晰地感覺到,有什麼東西飛快地掠過去了,一去不復返了。深藏在腦海裡的隱秘之核突然被打開,在陽光下消失於無形。電話裡傳來的那個聲音不是遠夏,而是一個三十歲的男人,身材開始變形,每天忙著上下班,接送兒子,給妻子做飯,不會再有時間玩『拳皇』,也不再會有心情彈《流浪歌手的情人》。
真正的遠夏已經永遠消失在那個夏天。
『``````雲寧,你現在高三了吧?學習怎麼樣?』電話那頭的男人問。
『不是很好。』
『「唉,要努力啊。爭取考到北方來。可以隨時到我這邊玩,多方便。』
『恩,我盡量。』
『什麼盡量嘛!一定要來!』
『恩,哥,我會的。』
我掛了電話,看了看天,整個世界突然如水般安靜。
『哥哥,我喜歡你,喜歡了整整四年。』這句話我終究沒有說出口。
也沒有必要再說出口了。
(32)
有些故事還沒講完那就算了吧。
那個初到北方的孩子,總是記不住從學校到姑姑家的路。
她坐在遠夏的自行車後架上,偷笑著聽哥哥用無奈的口氣訓斥說:
『雲寧,你這個白癡丫頭!說過多少遍了,回去的方向是向南,拐彎,再向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