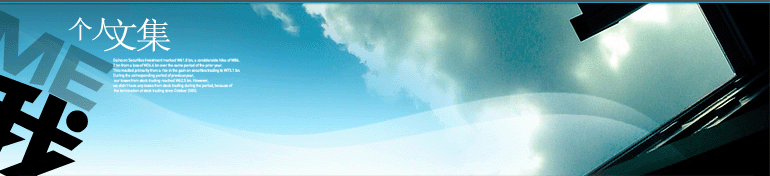|
曾經有一個叫清風的人對我說:『寧子,你看天多藍。』我駐足,用力得仰起脖子,望天。是的,天很藍。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特別的孩子,特別的熱愛寂寞的感覺,特別的喜歡仰望天空,特別歡欣的微笑。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想走近你可是我什麼也不能說你要我怎麼辦我比誰都更加疼痛更加害怕疼痛而你怎麼會懂
二月。早春,我沒有看到楊柳發芽。許是去年冬天太暖和了,這些樹的葉子竟然大半未落。以前,我習慣在騎車的時候,空出一只手來,去觸摸路邊垂柳的枝條,偶爾捋下一兩片葉子,感受它們在指間片刻的柔軟,然後揚起手來,它們便飛快的從我指縫中逃逸出去,毫不留戀。可我現在夠不著那些枝條了。它們空蕩蕩的垂下來,對我袒露著那些被粗暴扯裂的傷口。我伸出手去,可是無能為力,就像朋友在我面前流血而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什麼忙也幫不上。我難過的想哭。詩牆大堤上的櫻樹,到現在都沒有開花。她們把季節遺忘了吧,遺忘在沈睡的夢裡。等到她們醒來,發現已經到了夏天,她們該怎麼辦?一切都比我預期的來得遲——一片雲,一只鳥,一個未完結的故事。但我的青春,早已走了,走得不留痕跡。在我垂首等待的時候,四季的輪回已過,而我甚至還來不及發出一聲嘆息。這是二月,一個適合歌唱的季節。有時候我會唱起歌,很小聲很小聲的唱。唱Beyond的歌,唱《海闊天空》,《光輝歲月》,唱《你知道我的迷惘》——一個人孤獨的時候,走道眼前擁擠的街頭,是在抗議過分自由還是荒謬的地球。一個人在受傷的時候,按著難以痊愈的傷口,究竟應該拼命奮斗還是默默地溜走...沒有人會聽得見我的歌唱。在二月裡,我還是習慣一個人寂寞的行走。盡管有羿,盡管他願意每刻都陪在我身旁。當我垂首的時候,當我沈默的時候,他會不斷的追問我:『寧子,你怎麼了?』我抬起頭,用我一慣的笑容,回答說:『沒什麼啊?我在構思我的小說呢。』於是他便放心地拍著我的肩,嘲笑我的胡思亂想。我也笑了,用力地笑,好像我剛纔真的是在構思一篇極荒誕的小說。然後天空就在我的笑聲中越來越遠。
一直不敢走近一條街。那條街上,曾有兩個孩子大聲的唱歌,唱Beyond的歌,唱《海闊天空,《光輝歲月》,《你知道我的迷惘》——我們曾經一樣地流浪,一樣幻想美好的時光,一樣地感到流水年華。我們雖然不在同一個地方,沒有相同的主張,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那兩個孩子,就是哥哥跟清風。還有一個孩子,遠遠的跟著他們——那就是我。我喜歡清風帶我一起靜靜地仰望天空,藍郁的天空,包容一切的天空,看大朵大朵的浮雲怎樣匆匆的聚集然後又倉皇的逃離,看飛鳥怎樣掠過不留痕跡——就算整個世界都遺棄我們,可是天空不會——清風對著天空說。而我的天空,在清風的眼睛裡。可是那片天空,現在在哪裡呢?
仰望星空的時候,總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很多事,想到清風,想到哥哥,想到從前的那些人,忽然覺得他們都離我好遠。他們把我孤零零地扔在一個角落,然後就走了。他們遠遠地對我微笑著說:』寧子,你該長大了。』我想哭,可是發不出聲音。沒有人比我更恐懼長大。清風跟我說:』沒有人會真正的愛我們,所以我們只有更愛自己;沒有人會真正理會你的哭泣,所以你只有笑得更多。『可是清風,連你也不肯理我了嗎?我一直在笑,非常努力地笑。所以羿對我說:』寧子,你好像從來不知悲傷,每天都這麼快活。』清風,我做到了。可是你為什麼連一個背影都不肯留給我?
清風說:『寧子,你一定要堅強。』我不說話。清風說:『如果有一天,我必須離開你了,你會怎麼辦?』我說:『我會祝福你。』清風笑了。他說:『那我走了。』他真的走了。我知道清風遲早會走的。他不屬於這兒,他也不屬於我。他屬於他的父親,那是他生命的支柱。可他父親得了癌癥。清風說他願意用他自己的生命來換回他父親的生命。可是清風,你知道嗎?我多想代替你來換回伯父的生命!清風走的時候,我沒有去送他。自那以後,我成了眾人眼中最快樂的人。
我原以為我會這麼快樂下去的,我原以為。盡管每次我騎車經過那條街口的時候都會停下來,抬頭仰望天空五分鍾,然後跳上車,繼續我的行程;盡管每次在夜裡聽到beyond的歌尤其是那支《你知道我的迷惘》時,眼淚會不可抑止的滑出眼眶;盡管我總是行走時將鴨帽檐壓得極低,總是伸出左手觸摸空氣,總是哼著一段重復的旋律。可是,沒有人會知道——平日裡,那個有著極張揚笑容的孩子,那個總是前呼後擁的孩子,那不是『我』。直到有一天,我的左手突然莫名的疼痛不止,然後收到一封陌生的來信,那個叫做普羅的人在信上說:清風的父親死了。他已經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我的身體陡然僵直,很久很久。黑色的風吹過,清風的聲音輕輕的回響:『寧子,你一定要堅強。』可是清風,你呢?你怎麼可以不堅強?
沒有人會知道我的悲傷,羿更不會不知道。二月的情人節,羿送給我的禮物,到現在我都沒有打開。我小心的避開羿的眼神,我知道那裡有的是期望和深深的失望。但我決不會讓羿看到我眼底的懮傷。羿,我是不能給你真正的快樂的。盡管你眼中的我一如既往的快樂。二月的風,輕輕地吹過,吹過窗臺,吹過我的掌心,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我所能做的,就是每夜對著這夜空,捂住星星的眼睛,這樣,它就不會看到,我在流淚。羿當然不會知道,其實一直以來,我喜歡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清風。沒人能懂,包括清風,包括我自己。在二月裡的歌唱,沒人聽到。
七月,我終於有了清風的消息。他發了一張照片到我的信箱裡,連著一封短短的信。照片上清風的眼睛安詳得像一泓湖水;嘴角微微地上揚,很恬適很溫和的微笑,是能讓人的心隨之沈靜下來的那種。信的結尾他說:寧子,天天天藍。看完信,我笑了笑,然後張開雙臂仰望天空。風從我指間掠過,流水一般的觸感,極溫柔。天空是漫無邊際的灰迷,可以掩飾一切遮蓋一切。那些曾經多麼熟悉的面孔。我的眼淚漸漸的盈滿眼眶,然而,始終沒有流出來。我很想告訴清風天不會總是藍的,就像那天。其實那個季節的天空一直未曾藍過。但是我什麼也沒有說。我最終沒有回信。
清風在南方海邊的一個城市裡,那裡的天藍得透明。清風曾說他最喜歡的就是碧海藍天。 可是對我來說,那座城市不過是遠得不可再遠的地平線,中間的距離是八年——清風年長我四歲,而自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算起,已經過了四個年頭。 8年,已經足夠兩個人從熟悉到陌生。那兩個曾經在天空下面放聲歌唱的孩子,到哪裡去了?我望著天空,緊緊地攥著左手,緊緊地,攥到疼痛,可是我卻攥不住一絲一毫屬於我的時光,那些一去不復返的時光。它們就這樣安靜的離開,而我只有在對面遠遠地觀望,成倍的難過。我的左手,已經比我的心更蒼老。 Beyond唱:『天依然蔚藍,你仿佛走過所有夜晚``````』
普羅留下一個電話號碼。我以為我能夠永遠不去碰它。那天,我終究還是忍不住,撥通了那個號碼。清風的聲音從那麼遙遠的地方傳來,清晰的不真實。他是普羅啊,我狠狠掐了自己一把。普羅說:『寧子,你好。我是清風的同事。清風跟我說起過你,你是他最喜歡的妹妹。』 『清風呢?』 『清風現在過的很好,他已經完成了一次涅磐的過程。』 『寧子,清風讓我告訴你,』電話那頭普羅的聲音飄忽,『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的。你是個堅強的孩子,一定可以過的很好。』我放下話筒,然後對著電話機說:『是的,我很堅強。』我的手心在一瞬間變的冰冷。然後就聽見陽光『啪』的一聲,不著痕跡的斷裂了。我想我要是沒有打這個電話該有多好,至少我還能保存一個真實的影子。
羿的生日會上,我喝了酒。冰冷的液體從脣間灌下,徑直穿過喉嚨,抵達胃部。我一口氣喝掉了兩瓶。羿在一旁柔柔的勸:『寧子,不要喝了。這樣喝酒很容易醉的。『我注視著羿的眼睛——深褐色的瞳仁裡所有的關懷與真誠一覽無餘。 『放心,我不會醉。』我重新端起酒杯。同桌的女孩子們起哄:『醉了,醉了,臉都紅成關公了。』 『要我證明嗎?』我說,『我清醒的很。不信我背詩給你們聽——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女孩子們哄聲更大:『還說沒醉,都開始說胡話了。』她們不相信我是清醒的,就像她們也不相信我是第一次喝酒一樣。鬧得最凶的一個女孩子說:『酒後吐真言。寧子,快說,你最喜歡的人是誰?』我沈默,只是不斷的倒酒。羿按住我的手:『寧子,你怎麼了?』 『羿,抱抱我。』我說。 『羿,我真的很喜歡你。』這是一個在所有人意料之中的答案。女孩子們都笑起來。羿眼睛亮亮的看著我。我知道那亮亮的光,叫做幸福。觸手可及的幸福。如此簡單。而那不是我想要的幸福。擁有碧海與藍天的清風,你已找到屬於你的幸福了麼?
很久以前,哥哥說:『羿,你為什麼總像個孩子?』我回答:『因為長大了就要負擔責任,我怕。』可我現在真的不是一個孩子了。 『寧子,你成熟的讓我們陌生。』羿的臉上寫著惶惑。我不懂得什麼叫成熟。我只知道,很多人的目光在背後看著我,他們說我應該這樣生活。這樣的我,會讓他們放下心。只是,當有一天連我自己也認不出自己,我該怎麼辦?沒有人告訴我答案。
我問羿,假如在碧海與藍天之間讓你做個選擇,你會選擇什麼?羿想了想說:『我選擇地平線。』為什麼? 『因為海離我太遠,天空太虛幻——而所謂的藍,不過是視覺的假象。』那地平線呢? 『永遠是一個開始,永遠保持著可以望見卻不能接近的距離,不使人絕望。』可也是一道界限,一個終點——這句話我沒有說出口。羿的回答已經足夠。任何回答對我來說都已經足夠。地平線——七月的一聲嘆息,消失在時間的背面,而我只有悄悄地、悄悄地轉過笑臉。我已不能再奢求什麼。閉上眼,我對自己說:『從今以後,開始幸福。』天空。大海。地平線。以及流浪的昨天。
很久以後接到普羅的電話。他說:『寧子,你還好嗎?』他說:『寧子,記得要在陽光下微笑。』 『恩。』我說。 『寧子,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其實我``````』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就是清風對嗎??』 『恩,寧子,原諒我一直沒說``````』 『我體會得到。我從來就沒有怪你!』 『恩,好妹妹。我們還能像從前一樣,對不對?』 『對!』我說。可是,已經有什麼東西不見了,再也回不來了。清風,你離我是那樣的遠,那樣的遠。我在哭泣,而你怎麼看得見?那個夏天,我也永遠的失去父親。
又到二月。再沒有人叫我孩子了,包括哥哥,包括清風。那些我以為可以依偎一輩子的人。我抬頭望天,天依然蔚藍。那顏色純淨的讓我恍惚:天空背後有一雙眼睛,孩童般的,對我微笑。應該微笑的,我們都應該微笑的。只是,我需要一個理由,讓我——一如既往的懮傷,或者,不將一個名字遺忘。
那些似曾相識的陽光那些已經失去的心情也許會在某一天孩子因為他再也找不回的世界,以及年輕哭泣的時候,告訴他什麼是堅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