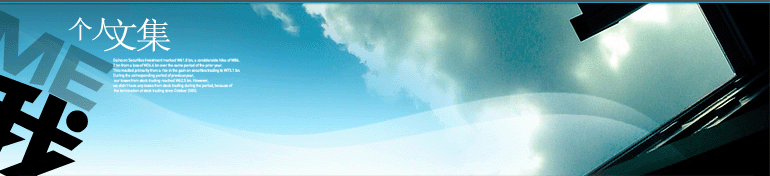|
『彤彤!你老實點,再不老實我揍你啊!』弟弟文剛大聲呵斥著他的女兒,我那4歲的小侄女。彤彤其實很乖巧,平時跟著爺爺奶奶,都很聽話。只是我一回家就會發飆。因為這個小東西知道只要我回家了,她就有了靠山就是闖了天大的禍我這個大伯也會替她扛著。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我趕忙把彤彤攬到自己懷裡,在她的小臉上親了一下。沒好氣地對文剛說:『你瞎嚷嚷什麼啊?孩子嗎當然就得調皮,能有什麼事啊。』
可能文剛對我早就有了意見,這回正好爆發了出來,瞪著眼睛衝我嚷開了:『你就寵吧,你看看你都把她寵成什麼樣了,只要你一回來就沒有她不敢乾的,打架,罵街,糟蹋東西。就沒有她不會的了。』
『她現在小,長大了自然就知道改了,你現在瞎咋呼什麼。』彤彤這個小東西更是裝做個小可憐一樣,把小臉紮在我的懷裡看也不看她爸一眼。我白了文剛一眼繼續說:『我還沒說你那,你把我家的浩浩慣成什麼樣了你怎麼不說啊。現在看見什麼要什麼一點規矩都沒有。』
聽我說這個文剛更火了:『你成天不在家,孩子想見你一回都得等三倆月的,我當叔叔的就不能疼啊,別忘了咱老徐家可就這個一個兒子。你不疼我還疼那,以後你少說是你兒子,你這個爸一點都不合格。』
『放屁!就這麼一個兒子?還就這麼一個閨女那,反正你以後少說我們彤彤的不是,給我知道我可跟你沒完。』
文剛是真急了,說話都哆嗦了:『你你你。。你怎麼不講理那你。你混蛋啊你。』
『你說誰混蛋啊?』
『說你!!就說你』
『啪!!』我一巴掌就打在了弟弟的臉上。
『啪!啪!』還沒等我反應過來,我爸也給我兩記耳光。『兔崽子!還瘋了你們了啊!從小不打架現在都長本事了是吧,會動手了啊!滾!都給我陽臺上跪著去,我不說話誰也別回來吃飯。』我們最少有10年沒有看見父親這麼生氣了,沒敢多嘴哥倆蔫蔫的走到陽臺上對著窗外的月亮跪了下去。
屋裡一家子誰也不敢再說什麼,只聽見父親粗重的喘氣聲,和母親小聲的安慰。窗外的夜空很晴朗,沒有一絲雲彩。月亮圓圓地掛在南天上,也不知道它是在笑還是在哭。反正透過它的光,我看見弟弟的臉上正掛著眼淚。
我看了文剛一眼,用手捅了他一下,說:『好了!都30來歲了,還掉什麼眼淚啊。我不是還挨了爸兩巴掌。扯平了啊』
『切!!』弟弟沒理我,只是用手抹了一把臉上的眼淚。
我對著月亮嘆了一口氣,繼續說:『記得咱們小時侯犯了錯,爸也是這樣罰我們到院子裡跪著不讓吃飯,嘿嘿!想想真的有好多年沒這樣了。』
『得了!哪次不是你犯錯我給你陪綁啊。你還有臉說。』文剛沒好氣地回了我一句。
『誰讓你是我弟弟那,你不陪我誰陪我啊。』話說著說著就走進了我們童年時的記憶。
我和弟弟只差了兩歲,但是弟弟比我長的高也壯,小時侯我們走在街上外人就分不出來我們到底那一個大那一個小。鄰居家的爺爺奶奶都說老徐家的這倆小子以後肯定有出息,以後都是乾大事的人。我們當時也不明白為什麼會這麼說,興許就是因為我們哥倆從小就和氣,從沒吵過嘴,更不用說打架了。應了那句老話和氣生財。
但是我們的童年家裡的日子並不好過,一家子都靠父親那幾十塊錢的工資過日子。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需要照顧,所以家裡的日子總是緊巴巴的。記得那一年暑假村外的鐵路在整修,路基下扔了好多換下來的水泥路枕。那裡面有鋼筋,村裡有好多人去砸了鋼筋賣錢。哪天我拉著弟弟找個兩把鐵榔頭也去了鐵路邊。水泥路枕好硬,一榔頭下去只能留下一個白點,而且還震的整條手臂都酸疼。弟弟的小手很快就起了水?。但是他還是一個勁的砸。『砰砰砰~』我們費了一個上午的力氣也沒砸掉一根路枕。快到中午的時候也不知道是熱的還是累的,弟弟的榔頭沒了准頭,一下子砸在了自己的左手的手指上。我只聽見他『哎呦』了一聲。我趕忙跑過去,抓起他的手一看就傻了,整個小指頭血肉模糊的。我哇的一聲就哭了出來,一邊用嘴給他吹,一邊哭著問:『弟弟,疼不疼啊,疼不疼啊?』
文剛興許是剛砸上的那個麻木勁不感覺有多疼,反而笑了,替我擦著眼淚說:『哥!我不疼,真的不疼,就是有點麻。沒事!你別哭。等我們長大了,掙好多的錢,僱人來砸。就不用我們費勁了。對吧』
晚上回家以後我們又被罰跪了,而且從那以後弟弟左手的小指頭就不能伸直了。一直到現在。那一年我11歲文剛9歲。
後來我們也漸漸長大了,家庭的負擔也越來越重。單憑父親那點工資供養我們兩個中學生根本就不大可能,弟弟的學習一直比我好,也許是繼承了父親的良好的大腦。成績一直都是年級第一。而我卻喜歡繪畫寫作,對學業並不是很重視。17歲那年弟弟考高中,靠上了市重點。但是家裡的經濟情況卻負擔不起,弟弟說不去了,就留在鎮上的高中讀書。父親沒有點頭只是看了我一眼。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站起來說:『讓弟弟去吧,我明天就去鎮上的機械廠上班,那裡正招工。』說完我就跑了出去,在村外的莊稼地裡大哭了一場。直到晚上纔回家。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機械廠上班了。從那以後我和弟弟就很少說話。漸漸的疏遠了。
轉眼幾年過去了,世界在轉瞬間變了摸樣原先的鄉村被城市吞並了,推倒了一片片的平房蓋起了高樓大廈。而我在這幾年中也歷經世間沈浮。原先的機械廠早已經不復存在。我做過很多的工作,給合資企業做過車間主管,給私營企業做過副廠長,還做個小商販和苦力。最後經過自己的努力開了一間計算機公司。生意還不錯,足可以改變一家人的生活面貌。當然其間也娶妻生子。弟弟的人生比我順利的多,昇大學,考研究生。最後被企業聘用為高級管理人員,一切都順理成章。但是我們之間的關系始終都有那麼點隔閡。不能逾越。
後來我的事業走下坡,公司面臨倒閉。家庭也不得安寧,妻子和我鬧離婚。我本就早已經厭倦了那段失敗的婚姻,不顧父親和母親的反對和前妻簽了離婚協議書。之後就一個人出走大西北。在蘭州的幾個月裡,每每想給家裡撥一個電話但是都會不自主的又掛掉了。
忽然有一天,我在我的住處附近的牆上看到了一張尋人啟示,是找我的。我摸著那張紙眼淚啊就再也止不住。等我回頭的時候,我看見文剛就站在我身後。他一下子就撲上來抱住我,大聲的哭著說:『哥!回家吧,家裡人都急瘋了,現在沒人怪你了,大家都知道你心裡苦。但是你得說出來啊,你不說說能了解啊。跟我回家吧,我找得你好苦啊。』原來弟弟已經在蘭州找了我快一個月了,公司幾次催他回去上班,他都沒有走。他說他出來的時候答應了父親一定要把我帶回去。
月亮的光照在我和文剛的臉上,我們對視著,笑著。相互給對方抹著眼角的淚水。我拉過弟弟的左手,輕輕撫摩著那根彎曲的小指。說:『弟弟,明天咱哥倆僱人砸鋼筋去。』
徐文彬
2005.8.18於天津
|